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回忆
过去包括物体、事件、情绪等的经验再次从记忆系统中被提取出来的过程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回忆(英语:Recall)指的是提取过往信息的心理过程,有时也可以指代提取的信息本身。回忆和收录、贮存[1]一并为记忆的三大核心过程。回忆一共分为三种类型:自由回忆[2]、线索回忆与序列回忆[3]。通过测试这三种回忆的方式,心理学家可以研究人类[4]和动物[5]记忆的过程。关于人类是如何回忆的,目前有两种理论:二阶记忆论,以及编码特定理论。
此条目可参照外语维基百科相应条目来扩充。 (2017年5月19日) |
理论
此理论指出,回忆过程涉及两个阶段,始于检索和取回过程,然后是决策或辨识过程,从检索到的资讯中取得正确的资讯。在这个理论中,辨识只涉及后一阶段/过程,这被认为是辨识过程相比回忆过程更占主导的原因。辨识只涉及一个可能发生错误或失败的过程,而回忆则涉及两个过程[6]。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回忆被发现优于辨识,例如无法辨识稍后可以回忆起来的单字[7]。
另一种两阶段理论认为,对一系列项目的自由回忆始于工作记忆中的内容,然后转向联想搜寻[8]。
编码特定性理论发现辨识过程和回忆过程之间存在相似之处。编码特定性原则指出,记忆利用来自记忆痕迹或学习资讯的情况以及检索资讯的环境中的资讯。换句话说,当编码时可用的资讯在检索时也可用时,记忆力就会得到改善。例如,如果一个人要学习某个主题并在特定位置进行学习,但在另一环境中参加考试,那么他们的回忆不会像在所学位置考试那样成功。编码特定性有助于考虑上下文线索,因为它专注于检索环境,并且它也实际说明了辨识可能并不总是优于回忆[7]。
历史
关于人们如何获得关于他们的世界的知识的哲学问题刺激了对记忆和学习的研究[9]。回忆是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记忆研究的历史总体上也提供了回忆研究的历史。

在1885年,赫尔曼·艾宾浩斯创造了无意义音节,即不符合语法规则且没有意义的字母组合,以测试他自己的记忆。他会记住一系列无意义音节,然后在不同的时间间隔中测试自己对这些音节的回忆。他发现,记忆的丧失在最初的几个小时或几天内迅速发生,随后的几天、几周和几个月内则显示出更稳定且逐渐的下降。此外,艾宾浩斯还发现,多重学习、过度学习和分散学习时间会增加信息的保留[10]。艾宾浩斯的研究对20世纪的记忆和回忆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弗雷德里克·巴特莱特是20世纪中叶记忆领域的重要研究者。他是一位英国实验心理学家,专注于人们在回忆新信息时所犯的错误。他的著作《记忆:实验社会心理学研究》于1932年出版,是他的知名作品之一。他以北美原住民的民间故事而闻名,包括《鬼魂之战》[11]。他会给研究参与者提供故事的摘录,然后要求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回忆[11]。记忆保持的时间间隔从阅读故事后立即到几天之后不等。巴特利特发现,人们会试图理解故事的整体意义。由于民间故事包含超自然元素,人们会将其合理化,使其更符合自身文化。最终,巴特利特主张,参与者所犯的错误可以归因于“模式侵入”[11]——当前的知识干扰了回忆。
在1950年代,记忆的整体研究发生了变化,这一变化被称为认知革命。这包括了新的记忆观念,常常将其类比为计算机处理模型。两本重要的书籍影响了这场革命:《行为的计划与结构》,由乔治·米勒(George Miller)、尤金·加兰特(Eugene Galanter)和卡尔·H·普里布拉姆(Karl H. Pribram)于1960年出版,以及乌尔里克·奈瑟(Ulric Neisser)于1967年出版的《认知心理学》[9]。两者均提出了对人类思维的资讯处理观点。艾伦·纽厄尔和司马贺构建了模拟人们在解决不同问题过程中的思维过程的计算机程序[12]。
在1960年代,对短期记忆的兴趣增加。在1960年代之前,对短期记忆及其快速记忆丧失的研究非常少。劳伊德和玛格丽特·彼得森观察到,当人们被给予一小串单词或字母,然后分心并忙于另一项任务几秒钟后,他们对该串单词的记忆会大幅下降[9]。 阿特金森和西弗林(1973)创建了短期记忆模型,这成为研究短期记忆的流行模型。[13]
在记忆回忆的研究中,下一个重要的发展是安道尔·图威提出的两种类型的记忆:情节记忆和语义记忆。图威将情节记忆描述为关于在特定时间和地点发生的特定事件的记忆,例如你在十岁生日那天得到的礼物。语义记忆则是长期记忆中储存的抽象单词、概念和规则[14]。 此外,图威于1983年提出了编码特异性原则,这解释了信息编码与回忆之间关系的重要性。更进一步解释,编码特异性原则意味着,如果回忆提示与编码提示相匹配或相似,个体更可能回忆起该信息[15]。
1960年代也见证了视觉意象及其回忆的研究发展。这项研究由艾伦·派维奥领导,他发现越是能引发意像的单词,更有可能在自由回忆或配对联想中被回忆起来。[16]
自1980年代以来,对记忆的运作,特别是对回忆的运作进行了大量研究。上述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改进,并且新的研究仍在进行中。
Remove ads
种类
回忆可分为三个种类。
自由回忆描述了人们获得一系列物品以记忆然后被测试的过程,他们被要求以任何顺序回忆这些物品[9]。自由回忆通常显示出首因效应和近因效应的证据。首因效应表现为个体更早且更频繁地回忆出列表开头的项目。近因效应则是当个体更早且更频繁地回忆出列表末尾的项目时的情况[9]。 自由回忆通常从列表的末尾开始,然后移向开头和中间部分。[8]
提示回忆是指当一个人获得一系列物品以记忆后,接着被提供提示以记忆材料的过程。研究人员使用这种程序来测试记忆。参与者会获得配对的词汇,通常的形式为 A1-B1, A2-B2…An-Bn(n 是列表中的配对数量)以进行学习。然后实验者给参与者提供一个词作为提示,以唤起他们回忆与之最初配对的词汇。词汇的呈现可以是视觉或听觉的。
用于进行提示回忆的基本实验方法有两种:学习-测试法和预期法。在学习-测试法中,参与者学习个别呈现的一系列词对。随即在学习阶段或过了一段时间后,参与者会接受测试,测试内容是刚刚学习的词对。每对词中的一个词以随机顺序呈现,参与者被要求回忆与之最初配对的项目。参与者可以测试正向回忆,即 Ai 被作为 Bi 的提示,或反向回忆,即 Bi 被作为 Ai 的提示。在预期法中,参与者看到 Ai,并被要求预测与其配对的词 Bi。如果参与者无法回忆出那个词,则会显示答案。在使用预期法进行的实验中,单词列表会重复,直到某个比例的 Bi 词被回忆起来。
提示回忆的学习曲线随着完成的试验次数的增加而系统性增加。这一结果引发了有关学习是否全有或全无的辩论。一种理论认为学习是逐步的,且每对词的回忆随着重复而增强。另一种理论则认为学习是全有或全无的,也就是说,人们是在一次试验中学习词对,记忆表现是由平均学习的配对决定的,其中一些在早期试验中学习到,有一些在后来的试验中学习到。为了检验这些理论的有效性,研究人员进行了记忆实验。在一项1959年发表的实验中,实验心理学家伊夫林·洛克及伊利诺伊大学的同事沃尔特·海默有一个控制组和一个实验组学习词对。控制组学习的词对经过重复,直至参与者学会所有词对。在实验组中,已学会的配对保持在列表中,而未学会的配对用先前单词的重新组合替换。洛克认为,如果学习是逐步的,即使配对未被正确回忆,两个项目之间的联系也会增强。他的假设是控制组的正确回忆概率会高于实验组。他认为重复会增强词对的强度,直到强度达到产生明显反应所需的阈值。如果学习是全有或全无的,那么控制组和实验组应以相同的速度学习词对。洛克的实验发现两组的学习速度差异不大。然而,洛克的工作没有解决争议,因为在他的实验中,他重新安排了替换的词对,这些词对比原始词对更容易或更难学习。在进一步探讨该问题的实验中,结果参差不齐。参与者学习了 Ai-Bi 配对一段时间后,回忆 Bi 的时间随着持续学习的试验而减少,这现象支持了逐步学习假设。[17]
另一种可以使用提示回忆来检验的理论是正向和反向回忆的对称性。一般认为正向回忆比反向回忆更容易,即正向回忆的强度强于反向回忆。对于长的字母或单词序列(如字母表),这通常是真实的。在一个观点中,也就是独立联系假设,正向和反向回忆的强度被假设为彼此独立的。为了确认这一假设,乔治·沃尔福德博士测试了参与者的正向与反向回忆,结果发现正向和反向回忆彼此独立。词对联系的正向回忆概率为0.47,而反向回忆的概率为0.25[18]。 然而,在另一个观点中,即联系对称假设,正向和反向回忆的强度大致相等并高度相关。S.E. Asch 和 S.M. Ebenholtz 在斯沃斯莫尔学院的实验中,参与者通过预期回忆学习了一对无意义的音节。在达到一定学习阈值后,参与者使用自由回忆进行测试,以确定他们能记起的所有配对和单个项目。这些研究发现反向联系远比正向联系弱。然而,当正向和反向回忆的可用性基本相同时,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大。[19] 包括 Asch 和 Ebenholtz 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独立联系假设的理念认为正向和反向回忆的平等强度与他们的假设相符,因为正向和反向回忆可以独立,但强度相等。然而,持联系对称论的学者则将该数据诠释为结果适合他们的假设。
另一项利用提示回忆进行的研究发现,学习在测试试验中发生。马克·卡里尔和帕什勒(1992年)发现,仅进行学习阶段的组别比具有测试-学习阶段的组别多出10%的错误。在仅学习阶段中,参与者获得 Ai-Bi,其中 Ai 是一个英语词,而 Bi 是一个西伯利亚尤皮克语词。在测试学习阶段中,参与者首先尝试回忆出以 Ai 为提示的 Bi,然后他们被显示 Ai-Bi 配对。这一结果表明,在参与者学会某些内容后,测试他们的记忆通过精神运作有助于以后的回忆。与再度学习相比,回忆的行为会在 Ai 和 Bi 之间创建新的、更持久的连结。[20] 这种现象通常被称为测试效应。[21]
另一项研究表明,在学习后立即测试列表时,最后几对记忆最佳。在五秒延迟后,最近学习的单词的回忆降低。然而,列表开头的词对的回忆仍显示出更佳。此外,在较长的列表中,可回忆的单词对的绝对数量更多,但在较短的词对列表中,回忆的词对比例更大。
有时在回忆词汇时会发生干扰。干扰是指当参与者根据该词对的提示试图回忆某个词时所犯的错误。干扰往往与没有被回忆起来的正确词具有语义特征上的相似性,或者在当前列表或先前学习过的列表的其他词对中已经学过,或与提示项接近时间。当两个项目相似时,可能会发生干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卡哈纳教授和马里克·伏特则研究了脸部相似性对脸名联系的影响。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想要确定记忆回忆的表现是否会随着研究集合中与提示脸相似的脸数而变化。如果脸在半径范围内相似,则这些脸被视为相似。该范围内的脸数称为邻域密度。他们发现回忆名字与脸部的准确性较低且反应时间较慢,尤其是在邻域密度更大的脸部。两张脸越相似,干扰的可能性就越大。当用脸 A 作为提示时,如果脸 A 和 B 相似,则可能会回忆起名字 B,这表明发生了干扰。正确回忆的概率来自拥有其他样貌相似的脸的数量。[22]
提示充当人们应该记住的指导。提示可以是几乎任何可能作为提醒的事物,例如气味、歌曲、颜色、地点等。与自由回忆相比,受试者被提示记住列表中的某个项目或以某种顺序记住列表。提示回忆也促进自由回忆,因为当提示提供给受试者时,他们将记住原本未回忆的列表项目。图尔文在他的研究中解释了这一现象。当他给参与者提供联想提示,以回忆原本未回忆且被认为遗失的项目时,参与者能够回忆起该项目。[23]
Remove ads
序列回忆是指能够按照发生的顺序回忆物品或事件的能力。[24] 人类储存物品于记忆并回忆它们的能力对于语言的使用至关重要。想像一下如果以错误的顺序回忆出一句话的不同部分。已发现能够以序列顺序回忆的不仅是人类,还包括一些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和一些非灵长类动物。[5] 想像一下混淆一个单词中音素的顺序,或有意义的声音单位,使得“slight”(轻微的)变成“style”(款式)。序列次序还帮助我们记住生活中事件的顺序,即我们的自传记忆。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似乎存在于一个连续体上,其中较近期的事件更容易按顺序记住。[24]
长期记忆中的序列回忆与短期记忆中的序列回忆有所不同。要在长期记忆中储存一个序列,必须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复该序列,直到它作为一个整体在记忆中被表现出来,而不是一系列项目。这样,就不需要记住项目及其原始位置之间的关系。[5] 在短期记忆中,立即序列回忆(ISR)被认为起源于两种机制之一。第一个是指 ISR 是项目与其在序列中的位置之间联系的结果,而第二个则是指项目之间的联系(又称为链接)。位置-项目关系不能解释近因效应和首因效应,或语音相似性效应。首因模型脱离了这两个假设,提出 ISR 源于激活水平的梯度,其中每个项目具有与其位置相对应的特定激活水平。[25] 研究支持了立即序列回忆的表现当列表是同类的(同一语义范畴)时要比异类(不同语义范畴)好得多。这表明语义表示对立即序列回忆表现是有益的[26]。短期序列回忆也受到类似音项目的影响,因为相比于不相似的项目,回忆较低(回忆得较差)。这在列表独立测试时(比较两个单独的列表,类似音和不相似音项目)以及使用混合列表进行测试时都是如此。艾伦·巴德利首次报告了这样一项实验,其中列表内的项目要么是互不相似的,要么是高度相似的。
有证据表明,节奏对竞争性的运动表现高度敏感。研究表明,有节奏的指尖敲击会对回忆产生破坏性影响,而聆听节奏一致的声音则无同样影响,表明敲击及相似任务的运动反馈干扰了排练和储存。[27]
在人类的序列回忆研究中,通常观察到八种不同的效应:
- 列表长度效应: 序列回忆能力随着列表或序列的长度增加而下降。
- 首因和近因效应: 首因效应指序列前面的项目更容易被回忆,而近因效应指最后几个项目回忆得更好。近因效应在听觉刺激中表现得更加明显,而不是在语言刺激中,因为听觉呈现似乎能够保护列表的末尾不受输出干扰。[28]
- 转位梯度: 转位梯度指回忆更倾向于认识一个项目是什么,而不是序列中项目的顺序。
- 项目混淆错误: 当错误回忆出某个项目时,往往会倾向以与该位置原始项目相似的项目作为回答。
- 重复错误: 这种错误发生在回忆序列时,如果序列中较早位置的项目又在另一位置出现时。这一效应在人类中是相当罕见的。
- 填补效应: 如果一个项目在早期位置被错误回忆,则接下来回忆的项目往往是被这一错误替代的项目。例如,如果序列是 '1234',而回忆开始为 '124',则下一项很可能是 '3'。
- 突出效应: 当上一个列表或测试中的一个项目在新的列表或测试中被意外回忆时,通常发生这一效应。这个项目可能会被回忆在其原始试验的位置上。[5]
- 单词长度效应: 短单词比长单词回忆得更准确。[29]
Remove ads
神经解剖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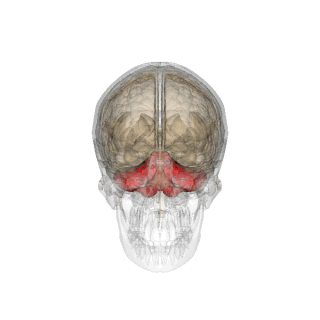

前扣带皮层、苍白球、丘脑和小脑在回忆过程中比识别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激活度,表明这些小脑-额叶通路的组成部分在回忆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在识别中并不发挥作用。尽管回忆和识别被认为是不同的过程,但这两者可能都是大脑区域分散网络的组成部分。[30]
根据神经影像数据,针对回忆和识别的正子断层造影研究一致发现以下六个大脑区域的区域性脑血流增加:(1) 前额叶皮质,特别是在右半球;(2) 颞叶中内侧的海马体和旁海马区域;(3) 前扣带皮层;(4) 包含后扣带、压后皮层、楔前叶以及楔叶的后中线区域;(5) 顶下小叶皮层,尤其是在右半球;(6) 小脑,特别是在左侧。[31][32]
这六个主要区域在情节检索中的具体角色仍不清楚,但有学者已经提出了一些想法,如右侧前额叶皮层与检索尝试有关;[31][32] 颞叶中内侧与有意识的回忆有关[33];前扣带则与反应选择有关[34];后中线区域与想像力有关[31][34][35][36];顶下小叶与空间意识有关[37] ;小脑则与自我发起的检索有关。[38]
在最近的研究中,一组受试者需要记忆一串项目,然后在尝试回忆这些项目时进行测量。研究发现在编码过程中测量到的诱发电位和血流动力学活动显示出随后被回忆的项目与未被回忆的项目之间存在可靠的差异。这一效应被称为后续记忆效应(SME)[39][40]。 这些特定大脑区域的差异决定了某个项目是否被回忆。费南迪斯(Fernandez)等人的研究显示,预测回忆的差异表现为在刺激呈现后400毫秒时嗅皮层(即环绕嗅脑沟的大脑皮层)中事件相关电位负偏离,以及在刺激开始后800毫秒时海马体的正向事件相关电位。[41] 这意味着只有当这两个大脑区域(嗅皮层和海马体)同步激活时,回忆才会发生。
影响回忆的因素
注意力对记忆回忆的影响会产生意想不到的结果。似乎注意力对记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编码阶段。在这个阶段,执行平行任务可能会大幅降低检索的成功率[42]。人们普遍认为,这一阶段需要大量注意力来正确编码手头的信息,因此,分心的任务无法允许正确的输入,从而减少学到的信息量。
人们对词汇的注意力受到情感抓取的影响。负面和正面的词汇比中性词汇更容易被回忆起来[43]。各种不同方式可以使人们专注于听取演讲者的讲话,包括演讲者语音的情感色彩,例如悲伤、满意或沮丧的语调,或使用那些触动人心的词汇[43]。一项研究旨在观察情感词汇的使用是否是回忆记忆的关键因素。各组被安排在相同的讲堂,听取相同的演讲者,而结果显示,听众所回忆出的语调和词汇选择得出结论:情感词语、短语和音调比中性演讲者的表达更令人难忘。[43]
回忆记忆与本能和机制有关。为了记住事件是如何发生的,以便从中学习或避免激怒者,人们会与情感建立联结。例如,如果演讲者非常冷静并且语气中性,则编码记忆的有效性非常低,听众只能理解演讲者在讨论的要点。另一方面,如果演讲者在高声喊叫或者使用情感驱动的词汇,听众往往会记住关键短语及演讲的意义。[43] 这是每个人在大脑中都具备的战斗或逃跑机制的完全激活,但触发该机制的因素将导致更好的回忆。人们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声音大、声音小或不寻常的提示上。这使得听觉系统能够捕捉到日常讲话和有意义讲话之间的差异,当在讨论中发言了某个重要的内容时,人们会集中注意力于演讲的那部分信息,但往往会忽略讨论的其他部分。[43] 我们的大脑能够感知语音中的差异,当这些差异发生时,大脑便会将这部分的语音编码进记忆中,并且这些信息可供将来参考使用。
Remove ads
动机是促使人们执行并成功完成手头任务的一个因素。在 Roebers、Moga 和 Schneider 于2001年进行的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分为强迫报告、自由报告和自由报告加激励三组。结果发现,每组回忆的正确资讯量并没有不同,但在接受激励的组别中,参与者提供的资料较准确。 这意味着鼓励参与者提供正确的资讯会促使他们更加准确。[44]然而,这一点仅在“成功”被认为是提供正确资讯的情况下成立。当人们认为成功是完成任务而非完成的准确性时,回应的数量会增加,但准确性则会降低。这显示出结果取决于参与者如何定义成功。在提到的实验中,被分配到强迫反应组的参与者整体准确性最低;他们没有提供准确反应的动机,甚至在不确定答案的情况下也被迫作出反应。
另一项由Hill RD、Storandt M和Simeone C[45]进行的研究测试了记忆技能训练和外部奖励对自由回忆串列单词的影响。与之前的研究结果相似,该影响在儿童中得到了观察,但与年长学习者形成对比[46]。
在没有干扰的情况下,回想一系列项目时有两个因素在起作用:近因效应和首因效应。当短期记忆用于记住最近的项目时,就会出现近因效应;当长期记忆对较早的项目进行编码时,就会出现首因效应。如果讯息输入和输出之间存在一段长于短期记忆保持时间(15-30秒)的干扰期,则可以消除近因效应。当一个人在回忆首因资讯之前获得随后的资讯来回忆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47] 然而,首因效应不受回忆干扰的影响。最后几项从记忆中消失是由于分散注意力的任务从短期记忆中转移了这些项目。由于它们没有被背诵和排练,它们没有被转移到长期记忆中,从而丢失了。像倒数这样简单的任务就可以改变记忆力;然而空白的延迟间隔没有效果。[48] 这是因为人们可以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继续排练工作记忆中要记住的项目。 Cohen (1989) 发现,如果在编码阶段实际执行某个动作,则在有干扰的情况下,可以更好地回忆该动作。[48] 研究也发现,回忆某些项目会干扰和抑制其他项目的回忆[49]。另一种想法和证据表明,干扰对近因度和首因度的影响是相对的,由比率规则(保持时间与项目之间的呈现干扰率的比例)决定,并且它们表现出时间尺度不变性[50]。
情境依赖效应在回忆中通常被诠释为证据,表明环境的特征作为记忆痕迹的一部分被编码,并可以用来增强对其他信息的检索[51]。 换句话说,当学习和回忆阶段的环境相似时,就能够回忆得更多。情境提示在检索新学习的有意义信息时似乎是重要的。在 Godden 和 Baddeley(1975)的一项经典研究中,通过自由回忆词汇表的实验表明,深海潜水员在学习和回忆环境之间有匹配时,回忆表现更佳。潜水时学习的词汇表在潜水时回忆得最好,而在陆地上学习的词汇表在陆地上回忆得最好。[52] 一个学术应用的例子是,学生在安静的环境中学习可能会在考试中表现得更好,因为考试通常是在安静的环境中进行的。[53]
研究显示,女性在情节记忆任务,包括延迟回忆和识别方面,表现普遍优于男性。然而,在工作记忆、即时记忆和语义记忆任务上,男女之间并无显著差异。神经心理学的观察指出,总体而言,先前的伤害对女性造成的影响通常比对男性更大。有学者提议,性别在记忆表现上的差异反映了处理信息所使用的策略的根本差异,而非解剖差异。然而,关于大脑不对称的性别差异受到形态学研究的支持,这些研究显示男性的左侧不对称性大于女性,这意味着男女在利用大脑两侧的程度上存在差异。[54] 此外,有证据显示女性存在负回忆偏差,这表明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容易回想起自己的错误。[55] 在1991年 Dan Yarmey 的一项目击证人研究中,他发现女性在对嫌疑人体重的回忆准确性上显著优于男性。[56]
研究还测试了男性和女性在一次演讲后能够回想起什么的信息差异。该实验涉及三位演讲者,其中一位为女性,两位为男性。男女被安排在同一个讲堂内,并由同一位演讲者进行讲解。结果显示,所有参与者对女性讲者所呈现的信息更容易回忆起来。[57] 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性别之间一个重要的差异,因为女性的声音在音质上表现更佳,涵盖低音和高音的范围。[57] 由于其音域范围,语义编码在刺激大脑听觉部件等频率上得以增强;[57] 这更能为耳朵的功能所共鸣。音调的变化使得特定单词与其音调相连,随着音调的变化,单词突出,这些差异有助于记忆的储存。[57] 回忆变得更加容易,因为大脑能够将单词与所说的声音进行联结。
性别之间的一个显著差异在于信息的处理方式及其后的回忆。女性更倾向于记住非语言线索,并将讨论的含义与手势相关联。[57] 而男性则偏向于遵从语言线索,他们的反应更多是基于讨论中实际的事实和用词,但演讲者声音的波动帮助他们维持记忆。[57] 另一个将男性和女性区分开来的差异是回忆他人的声音。[57] 男性对他们所阅读的信息的回忆表现更好,例如物品清单,而女性则相对较弱。[57] 唯一的相似之处在于当使用情感词汇或产生情感音调时,男性和女性对这些变化的回忆均有所增强。[57]
现象
回忆的现象学解释称为元认知,或称为“对认知的认知”。这包括许多意识状态,被称为知识感状态,例如“舌尖现象”。有研究表明,元认知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使大脑能够观察处理中的错误,并主动投入资源来解决问题。元认知被认为是认知的重要方面,能够帮助发展有效的学习策略,这些策略也可以适用于其他情境。[58]
元认知的运作使我们能够评估自己的知识和理解,进而调整学习和回忆的策略。举例来说,当一个人处于舌尖现象时,即无法想起某个词语但感觉它就在脑海中,这种感知促使他们可能会试图使用不同的策略来检索信息。这显示出元认知不仅限于对知识的了解,还涉及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利用这些知识以达成学习目标。通过提高元认知技巧,学习者可以更加灵活地适应新的学习环境和挑战。
改善和帮助回忆记忆的一个关键技术是利用记忆术和其他认知策略。记忆术是一种认知策略,可以使个人更容易地记住和回忆新信息,而不单单是记住一系列无关的信息。[59] 一个记忆术的例子是PEMDAS(Please Excuse My Dear Aunt Sally),这是用来解决算式中括号、指数、乘法、除法、加法和减法的顺序的设备。单词或首字母缩略词可以代表个人需要回忆的过程。使用这类策略来执行任务的好处在于编码变得更为有组织,且信息的记忆和处理变得容易。[59] 此外,这种设备减少了在检索时需要有意识资源的需求,这意味着回忆不需要外部来源的帮助来记住昨日发生的事情。[59]
认知策略可以利用语义连结,这样大脑可以比仅仅将信息视为整体来得更高效地处理和运作。通过使用策略,信息之间变得相关,并且信息更容易被记住。[59] 另一种人们使用以提高回忆效率的设备是分块法(chunking)。分块是将数字分解成较小单元的过程,以帮助记住信息或数据,这对于记忆数字和数学事实非常有帮助。[64] 例如,电话号码通常被分块为三位数、三位数和四位数,这样在重述时更为便捷。研究表明,这些技术的效果明显,一个机构测试了两组人,以了解这些设备对实际人员的效果,结果显示使用认知策略的组别表现显著优于不使用这些策略的组别。在前测和后测中,使用技术的组别有所改善,而另一组则没有。[59]
地点法(Method of Loci, MOL)指的是个人通过想像一个空间环境来改善后续信息的回忆。与其单纯阅读一系列项目,个人可以在心中走沿着一条路径,将需要记住的东西放在不同的位置。这种精细的排练提供了在编码过程中操控信息的机会。例如,当你需要购买花生酱、牙膏、狗食和洗衣液时,可以想像自己先吃个花生酱三明治,然后走向浴室刷牙,接着经过狗的身边去洗衣房。这种提高回忆的方法似乎不仅限于回忆清单。研究显示,这种认知策略提高了学生在考试中的表现。参与者被分为两组,每组接受相同的医学讲座,后续进行自学或使用地点法。随后,两组都接受了相同的考核,使用地点法的组别表现更好,正确答题的数量更多。[60]
舌尖现象(Tip-of-the-Tongue,TOT)指的是一种感知,体现在识别或了解特定主题的情况下,无法回忆与该主题相关的描述词或名称的较大差距。这一现象也被称为“presque vu”,这是一个法语术语,意为“几乎看见”。舌尖现象有两种普遍的观点:心理语言学观点和后设认知观点。
心理语言学将舌尖现象视为从经语义记忆(事实)提示的词汇记忆中检索失败。由于随着年龄的增长,舌尖现象的频率有明显上升,因此心理语言学中有两种机制可以解释这一现象。第一种是随着年龄增长,词汇网络的退化,这导致知识的提示与词汇之间的连接减少,使得成功从记忆中检索单词的难度增加。第二种观点认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经验和词汇的积累会导致类似的情况,其中多样化的词汇与多样的知识之间的众多连接也增加了从记忆中成功检索单词的难度。[61]
元认知观点则将舌尖现象视为在这种事件发生时所感受到的意识和相应的经验感知。对舌尖状态的意识可以迅速调集认知资源以解决该状态并成功检索出单词。这样的解释虽然仍有待完善,但心理语言学观点与元认知观点并不互相排斥,两者均可用于在实验室环境中观察舌尖现象[61]。
舌尖现象中还可以观察到一种孵化效应,时间的推移本身可以影响该状态的解决并导致成功的回忆。此外,存在舌尖状态是一个良好的预测指标,表明问题可以正确解决,尽管这种情况在年轻成年人和老年人中出现的频率低于年龄较大的年轻成年人。这证实了元认知观点以及心理语言学观点。这表明资源被调用来搜寻记忆,寻求所需的正确信息,同时也显示出我们意识到自己知道或不知道哪些信息。[62] 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在将舌尖现象视为检索失败的心理语言学观点与将舌尖现象视为学习工具的元认知观点之间的辩论仍在持续的原因。
类似的现象包括既视感、犹昧感和既听感(déjà entendu)。这些现象发生的频率较低,并在有创伤性脑损伤或脑部疾病(如癫痫)的患者中更为普遍。
经常地,即使在数年之后,曾经存在于意识中的心理状态会在看似自发的情况下重返意识,而无需任何意志行为;换言之,它们是不由自主地再现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立即认出回归的心理状态是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也就是说,我们记得它。然而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伴随的意识是缺失的,我们只能间接地知道“现在”必须与“当时”相同;然而,这样的方式仍然提供了一种不亚于存在的有力证据,以证明其在这段时间内的存在。根据更精确的观察,这些不由自主的再现并不是完全随机和偶然的。相反地,这些现象是通过其他即时存在的心理映像得以引发的。此外,它们以某种规律的方式发生,通常被描述为所谓的“联结法则”。[63]
——赫尔曼·艾宾浩斯 (1885), 翻译自 Ruger & Bussenius (1913)
直到最近,针对这一现象的研究相对罕见,仅识别出两种类型的不由自主的记忆检索:不自主自传式记忆检索和不自主语义记忆检索。这两种现象可以被视为其他正常且相当有效的认知过程的突现方面。
不自主自传式记忆(IAM)检索是由感官提示和内部提示(如思考或意图)自发产生的。这些提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我们,通过启动效应持续而自动地激活内隐记忆。[64] 许多研究已证明,我们的具体目标和意图最频繁地导致相关的IAM的检索。而第二多的IAM检索则来自环境上下文中的物理提示。第三种、即与任何特定提示(无论内部还是外部)无关的自传式记忆是最不常发生的。有人提出,在这种情况下,记忆的自我调节发生了误差,导致不相关的自传式记忆进入了意识中。这些发现与元认知一致,因为第三种体验往往被识别为最显著的体验。[65]
不自主语义记忆(ISM)检索或称“语义弹出”,其发生方式与IAM检索相同。然而,诱发的记忆缺乏个人基础,通常被认为是微不足道的,比如随机的单词、影像或短语。ISM检索可以由激活扩散引发,在这种情况下,单词、思想和概念持续激活相关的语义记忆。当足够的相关记忆被提示,导致某个相互关联的概念、单词、思想或影像“弹出”到意识中时,当事人并不知道它的相关性在其记忆中的程度。激活扩散被认为是在许多小时、日子,甚至几周的时间内逐渐累积,直到一个随机的语义记忆“弹出”。[66]
参考资料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