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禁烟
政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烟草控制(Tobacco control),常称禁烟或控烟,是一门关注并旨在减少烟草使用的公共卫生科学、政策与实践,目标在于降低烟草造成的发病率和死亡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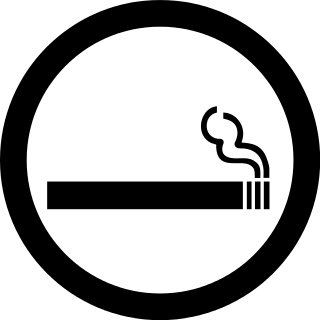
烟草控制政策涵盖多个层面,包括立法限制在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吸烟、设立无烟环境、规范烟草产品的制造、行销与销售等。由于绝大多数的香烟、雪茄和水烟含有烟草,因此这些产品是烟草控制的主要对象。此外,电子烟和加热烟等新兴尼古丁产品,因其对公共卫生的潜在影响,也逐渐被纳入全球烟草控制的范畴。[2]
历史
世界上最早的禁烟令之一是1575年罗马天主教会的一项规定,禁止在墨西哥的任何教堂内使用烟草。[3] 1590年,教宗乌尔巴诺七世采取行动,反对在教堂建筑内吸烟。[4] 他威胁将任何“在教堂门廊或内部,无论是咀嚼、用烟斗吸食,还是以粉末形式从鼻子吸入”烟草的人逐出教会。[5] 教宗乌尔巴诺八世于1624年也实施了类似的限制。[6] 1604年,英王詹姆士六世及一世发表了一篇反烟论文《烟草的还击》,其效果是提高了烟草税。从1627年起,俄罗斯禁止烟草长达70年。[7] 奥斯曼帝国苏丹穆拉德四世于1633年禁止在其帝国内吸烟,并将吸烟者处决。[6]
欧洲最早的全市范围禁烟令不久后便颁布。这类禁令于17世纪晚期在巴伐利亚、萨克森选侯国以及奥地利的某些地区实施。柏林于1723年、哥尼斯堡于1742年、斯德丁于1744年相继禁烟。这些禁令在1848年革命中被废除。[8] 在1865年之前,俄罗斯曾禁止在街头吸烟。[9]
烟草控制的历史,特别是在美国,充满了公共卫生倡议与烟草业强大阻力之间的持续博弈。自1964年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发表第一份关于吸烟危害的报告以来,许多联邦立法尝试虽然表面上是公共卫生的胜利,但往往伴随着对烟草业有利的妥协,甚至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10]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1965年的《联邦香烟标示和广告法案》(Federal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在公共卫生倡导者的推动下,该法案要求在所有香烟包装上标示健康警语。然而,在烟草公司的强力游说下,法案中加入了一项关键的“优先适用条款”(preemption clause),禁止各州或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规管烟草广告。这项条款极大地限制了地方层级的烟草控制权力,使烟草业免于应对各地区可能出现的更严格广告限制。尽管公共卫生界获得了警示标语,但这些标语的实际效果备受质疑,反而为烟草业在日后的个人责任诉讼中提供了“消费者已被警告”的法律挡箭牌。因此,该法案被后世评价为“为烟草业利益服务的程度远大于公共卫生”。[10]
另一项具有讽刺意味的立法是1969年的《公共卫生香烟吸烟法案》(Public Health Cigarette Smoking Act),该法案禁止在电视和广播上播放香烟广告。尽管这被誉为公共卫生的胜利,但它同时也终结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公平原则”在烟草议题上的应用。该原则曾要求电视台播放与烟草广告数量相当的反烟公益广告,这些公益广告在当时已证明能有效降低香烟消费。广告禁令生效后,烟草业将其庞大的广告预算转移到平面及户外媒体,而强有力的反烟声音却从广播媒体中消失。结果,在禁令实施后的短期内,美国的香烟消费量不减反增了4.1%。[10]
烟草业在应对其他控制措施时也展现了其高超的策略。例如,虽然烟草业一贯反对提高烟税,但当增税法案通过时,他们会借机将价格提升到远高于税收增加的幅度,并将涨价归咎于政府,从而实现利润的大幅增长。在1981至1985年间,美国一包香烟的平均价格上涨了36美分,其中仅11美分是新增的烟税,而高达19.2美分则直接转化为烟草公司的营业收入。[10] 在应对二手烟(ETS)问题上,当二手烟的危害开始动员非吸烟者支持禁烟政策时,烟草业发起了大规模的“宽容”运动,宣传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应互相尊重,并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OSHA)提出室内禁烟提案时,策动了大规模信件抗议活动,成功地延宕了联邦层级的室内空气质量规管。[10] 此外,对于任何暗示尼古丁具有成瘾性的说法,烟草业都予以激烈反击,甚至不惜在1994年对美国广播公司提起高达100亿美元的诽谤诉讼,仅因其节目声称烟草公司在香烟中“掺入”尼古丁以维持成瘾性。此举产生了寒蝉效应,导致媒体在报导烟草议题时更为谨慎。[10] 这些历史事件凸显了烟草业在影响公共政策和舆论方面的巨大能量,也为后来的烟草控制策略提供了宝贵的教训。
Remove ads
证据基础

研究已产生证据,证明二手烟会导致与直接吸烟相同的问题,包括勃起功能障碍[11][12](吸烟因促进动脉粥样硬化而导致勃起功能障碍)[13]、肺癌、心血管疾病以及肺部疾病,如肺气肿、支气管炎和哮喘。[14] 具体而言,统合分析显示,终生不吸烟者若与在家吸烟的伴侣同住,其罹患肺癌的风险比与不吸烟者同住的人高出20-30%。在工作场所接触二手烟的非吸烟者,其肺癌风险增加16-19%。[15] 由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召集、美国国家医学院发布的一份流行病学报告指出,接触二手烟会使罹患冠状动脉心脏病的风险增加约25-30%。数据显示,即使是低水平的暴露也存在风险,且风险随暴露程度增加而增加。[16]
世界卫生组织辖下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于2002年发布的一项研究结论指出,非吸烟者因烟草烟雾而暴露于与主动吸烟者相同的致癌物质。[17] 从烟草产品燃烧端释放的侧流烟[18]含有69种已知的致癌物,特别是苯并芘[19]和其他多环芳香烃,以及放射性衰变产物,如钋-210。[20] 烟草公司自己的研究已显示,数种公认的致癌物在二手烟中的浓度高于主流烟。[21]
确认二手烟影响的科学组织包括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22]、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23]、美国国家卫生院[24]、美国公共卫生局[25]及世界卫生组织。[26]
Remove ads
对酒吧和餐厅的吸烟限制可以显著改善这些场所的空气质量。例如,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网站上列出的一项研究指出,纽约州的全州性法律,旨在消除封闭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的吸烟行为,大幅降低了纽约西部的餐饮服务场所的可吸入悬浮粒子(RSP)水平。在法律实施前允许吸烟的每个场所,RSP水平都有所降低,包括那些在基线时仅观察到来自相邻房间烟雾的场所。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结论是,他们的结果与其他研究相似,这些研究也显示在实施禁烟令后,室内空气质量得到显著改善。[27]
2004年的一项研究显示,新泽西州的酒吧和餐厅的室内空气污染水平是邻近的纽约市的九倍以上,而纽约市当时已经实施了禁烟令。[28]
研究还表明,改善的空气质量转化为员工接触到的毒素减少。[29] 例如,在实施吸烟限制的挪威场所的员工中,测试显示吸烟和非吸烟工人的尿液中尼古丁水平均有下降(与实施无烟政策前相比)。[30]
2009年,美国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的全国性项目办公室“公共卫生法律研究计划”发布了一份证据摘要,总结了评估特定法律或政策对公共卫生影响的研究。他们指出:“有强有力的证据支持禁烟令和限制措施是旨在减少二手烟暴露的有效公共卫生干预措施。”[31]
许多吸烟者随意丢弃烟蒂,这些烟蒂很容易进入生态系统。烟蒂含有高浓度的尼古丁,对大多数动物来说是一种致命的毒素。许多动物,包括婴幼儿,可能会摄入这些烟蒂,面临尼古丁中毒的直接威胁以及摄入塑胶的相关危险。此外,燃烧的烟蒂可能引发野火。将烟蒂丢入下水道会导致排水管堵塞和随后的洪水。[32]
烟草种植也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首先,它导致森林砍伐,全球约5%的森林砍伐与烟草种植有关。据估计,每生产300支香烟就会损失一棵树。森林砍伐导致气候变迁、生物多样性丧失、土壤侵蚀和水污染。其次,烟草种植需要大量肥料,导致土壤退化和污染。一些肥料甚至含有放射性物质,这些物质可能转移到吸烟者和接触二手烟者的肺部。此外,烟草种植消耗大量水资源,加剧了水资源短缺。过度使用杀虫剂会污染水源、伤害野生动物,并对烟农构成健康风险,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那里可能缺乏安全知识且童工现象普遍。烟草生产还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加剧气候变迁。烟草废弃物污染海洋、河流、土壤和城市环境。在发展中国家,烟草种植引发了粮食安全问题,因为宝贵的水和农田被用于种植烟草而非粮食作物。总体而言,烟草种植对环境和人类健康都造成严重损害,有必要采取措施减少其负面影响。[33]
Remove ads
全球框架公约与MPOWER策略
为应对全球烟草流行,各国在《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指导下,已实施了一系列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世界卫生组织(WHO)为协助各国加速推动烟草控制,将其中六项基于证据的核心措施整合为MPOWER政策包。这六项策略相辅相成,当全面实施时能发挥最大效果,共同营造一个不利于烟草消费的社会环境。[2]
提高烟草产品的税率与价格,被公认为是降低烟草消费最有效且成本效益最高的单一干预措施。[1] 经济学研究一致显示,烟价与消费量之间存在明确的负相关。一般而言,烟价每提高10%,在高收入国家可降低约4%的吸烟率,在中低收入国家则效果更为显著。[34] 高烟价能有效阻止青少年开始吸烟,并促使经济能力较弱的吸烟者戒烟或减少吸烟量。一个显著的实例是菲律宾于2012年推行的“罪恶税改革”(Sin Tax Reform),该政策大幅提高烟草和酒精税,不仅成功降低了吸烟率,更将增加的税收专门用于资助全民健康保险,实现了公共卫生与财政收入的双赢。[35] 澳洲和英国等国也长期透过维持高烟税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吸烟率下降。[1] 尽管证据充分,但烟草税仍是MPOWER措施中,在全球范围内达到最佳实践水平最低的政策之一。[2]
制定并执行全面的无烟法律,禁止在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及公共交通工具中吸烟,是保护非吸烟者免受二手烟危害的根本措施。科学证据表明,二手烟并无安全暴露水平,即使短暂接触也会对健康造成危害。例如,爱尔兰于2004年成为全球首个实施全国性工作场所(包括酒吧和餐厅)禁烟的国家。政策实施后,不仅酒吧员工的呼吸系统健康状况显著改善,国家的心血管疾病住院率也随之下降,同时对餐饮业的整体经济并未造成负面影响。[10] 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市在实施禁烟令后的18个月内,心脏病发作住院率下降了27%。[36]

为吸烟者提供戒烟支持,是烟草控制策略中帮助个体摆脱成瘾的关键一环。有效的戒烟服务体系应包括由医疗专业人员提供的简短建议、戒烟热线、行为咨询以及药物治疗,如尼古丁替代疗法的尼古丁贴片、尼古丁咀嚼锭等。研究显示,使用NRT可以将戒烟成功率提高一倍。[10] 以英国国民保健署(NHS)为例,其提供全面的免费戒烟服务,包括一对一咨询、团体支持和处方戒烟药物,成为全球戒烟服务的典范。为提高可及性,许多国家如美国已将NRT产品转为非处方药,使吸烟者能更便捷地获取。[10] 美国《临床实践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也强调,医护人员应在每次就诊时主动询问患者的吸烟状况并提供戒烟建议。[37]

透过烟品包装直接向消费者传达烟草的健康风险,是一种高效率、广覆盖的宣传方式。采用大面积、醒目的图文健康警示,能有效打破烟草业透过精美包装营造的品牌形象,增加吸烟者对健康危害的认知,并激发其戒烟动机。[1] 更进一步的措施是推行简易烟盒计划,即统一烟盒的颜色、字体,并禁止使用品牌标志,仅保留标准化的品牌名称和健康警示。例如,加拿大是全球最早采用大幅图文警示的国家之一,其经验证明这项措施能有效提升公众对吸烟风险的了解。[1] 澳洲在2012年率先实施素面烟品包装法案,研究显示该政策成功降低了烟盒的吸引力,减少了品牌对消费者的误导,并强化了健康警示的效果。[1] 目前,图文警示是MPOWER措施中覆盖人口最广的政策之一。[2]

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对于防止烟草业误导公众、吸引新使用者(特别是年轻人)至关重要。这不仅包括传统媒体(如报纸、电视)的广告,也涵盖销售点的陈列、品牌商品、体育文化活动赞助以及网络行销等间接宣传手段。研究指出,全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的禁令能使吸烟率下降约7%,在某些国家甚至更高。[2] 历史经验提供了重要的教训。例如,美国在1971年禁止了广播电视烟草广告后,烟草业迅速将庞大的行销预算转移至平面媒体、户外看板和体育赞助,导致烟草消费量在短期内甚至出现反弹。[10] 这凸显了唯有“全面”禁止所有行销渠道,才能有效遏制烟草业的影响力。尽管此措施效益显著,但在全球范围内,尤其在高收入国家,其执行率仍然偏低。[2]
建立持续、系统的监测机制,是制定、评估和改进烟草控制政策的基础。透过全国性的调查,可以追踪烟草使用(包括各类产品)的流行率、相关的健康与经济负担,以及各项干预措施的成效。高品质的数据有助于识别高风险人群,并为政策调整提供科学依据。具体实例包括美国的“烟草与健康人口评估”(PATH)研究,这是一项大型全国性纵贯性研究,旨在长期追踪烟草使用行为及其健康影响,为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烟草监管决策提供重要数据。[38] 在国际层面,“国际烟草控制政策评估项目”(ITC Project)在超过29个国家进行,旨在评估《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各项政策在不同国家的实施效果,为全球烟草控制提供了宝贵的跨国比较数据。[38]
公共卫生影响与成效
全球范围内的烟草控制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全球15岁以上人群的吸烟率已从2000年的27%下降至2022年的约20.9%。据估算,若无这些政策干预,目前的吸烟者人数将会多出3亿。[2] 实施全面烟草控制政策的国家,其吸烟率均出现明显下降。例如,巴西在推行包括广告禁令、图文警示和高税率在内的综合政策后,成人吸烟率从1989年的34.8%降至2019年的12.6%,估计避免了数十万人因烟草相关疾病死亡。[1] 禁烟令的实施也能立即带来公共卫生效益,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在实施公共场所禁烟后,因急性心肌梗塞和哮喘等疾病的住院率显著下降。[39]
除了健康效益,烟草控制还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它不仅能节省大量因治疗烟草相关疾病而产生的医疗开支,还能通过改善劳动力健康状况来提升社会生产力。世界银行的研究指出,投资于烟草控制的每一美元,平均可带来数十美元的经济回报。[1]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社会规范的转变。持续的烟草控制努力有助于“去正常化”(denormalization)吸烟行为,改变社会对吸烟的接受度,使其不再被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交行为。这种文化上的转变对于预防青少年接触和开始吸烟尤为重要。[40]
挑战、争议与批评
尽管烟草控制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和批评。
烟草业及其利益相关者是烟草控制政策推进的最大阻力。[2] 他们采取的策略包括:透过政治游说、竞选捐款等方式影响立法,或对已颁布的禁烟法规提起诉讼,以延迟或削弱政策实施。[10] 烟草业还会资助或进行有利于己的“科学研究”,质疑二手烟危害的证据,或夸大禁烟政策对经济的负面影响。[2] 此外,他们也透过赞助体育、文化活动或推出环保项目等“企业社会责任”伪装,塑造正面形象,以转移公众对其产品危害的注意力。[41] 为应对此问题,《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明确要求缔约方保护其公共卫生政策不受烟草业商业及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

电子烟、加热烟等新兴产品的普及为烟草控制带来了新的复杂性。支持者认为这些产品可作为传统香烟的减害替代品,但反对者担心其对青少年的吸引力,可能导致尼古丁成瘾,并成为吸食传统香烟的“入门砖”(gateway effect)。[2] 这些产品的长期健康影响尚不完全清楚,其产生的气雾也并非无害。[2] 此外,监管也面临困境。例如,美国FDA在《烟草控制法案》实施后的十年中,其对电子烟的“上市前审查”(premarket review)流程被批评为本末倒置,客观上助长了青少年电子烟的流行。[42] 追踪这些产品的使用模式也极具挑战,需要如PATH研究这样的大型纵贯性数据来理解使用者在不同产品(单独使用或多重使用)之间的转换行为。[38]
许多国家,特别是中低收入国家,虽然制定了禁烟法律,但因资金不足、执法能力薄弱、公众意识不高等原因,导致政策执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1] 在美国等已建立监管框架的国家,挑战则更多体现在监管机构的“政治意愿”上。批评者认为,FDA在烟草控制上时常表现出过度谨慎甚至瘫痪,而非采取大胆果断的行动,导致许多关键政策(如薄荷醇禁令)被长期搁置。[42] 这种“缓慢的步伐”使得烟草业有充分的时间来应对和破坏监管措施。
部分反对者认为,禁烟政策过度干预了个人选择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私有财产所有者的经营权。然而,主流公共卫生观点认为,当个人行为(如吸烟)对他人健康构成威胁时,公共利益应优先于个人自由。[43] 关于经济损失的担忧,尽管部分餐饮和娱乐业者担心禁烟会导致顾客流失,但大量独立研究表明,禁烟令对这些行业的整体经济影响通常是中性或正面的,因为无烟环境会吸引更多非吸烟顾客和家庭消费。[44]
烟草控制政策在不同社会群体间的影响存在差异,这引发了对健康公平的深切关注。例如,提高烟税虽能有效降低总体吸烟率,但可能加重低收入成瘾者的经济负担。因此,政策制定需要辅以针对弱势群体的戒烟支持和补助措施,以确保烟草控制的益处能惠及所有人。[42] 更为严峻的是,烟草业常针对特定族群进行掠夺性行销,造成了严重的健康不平等。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美国烟草业几十年来针对非裔美国人社区进行薄荷醇香烟的精准行销。然而,2009年美国《烟草控制法案》在禁止调味烟的同时,却给薄荷醇开了一个“可耻的例外”。这一妥协被批评为“立法的代价往往由最无力负担的人——那些被不成比例影响、权力最小的群体——来支付”,是烟草控制中亟待解决的社会正义问题。[42]
各国/地区状况
全球已有183个缔约方批准了《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但各国的执行进度和成效参差不齐。[2] 根据烟草流行的发展,各国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流行初期(男性吸烟率<15%);第二阶段为流行上升期;第三阶段为流行高峰或初步下降期;第四阶段为流行大幅下降期(吸烟率<25%)。[2] 许多非洲和中东国家的男性吸烟流行仍处于上升期,而欧洲、东亚和北美大部分地区则处于第三或第四阶段。女性的烟草流行通常比男性晚数十年,在许多地区仍处于初期阶段,这也为预防工作提供了机会之窗。[2]
MPOWER各项措施的全球实施水平也极不均衡。截至2024年,图文健康警示是覆盖人口最广的措施,而烟草税则是实施程度最低的最佳实践措施之一。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TAPS)在中低收入国家的采纳率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2]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全球仍有近20亿人未受到任何一项最高标准的MPOWER措施保护,显示出全球烟草控制工作的巨大差距。[2]
 中国大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口超过3亿。中国已批准FCTC,并在多个城市(如北京、上海)实施了严格的公共场所禁烟条例。然而,国家层面的全面禁烟立法进展缓慢,烟草专卖制度以及烟草利税在财政中的重要性,为烟草控制带来了独特的挑战。[45]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0年中国男性超过20%的死亡归因于吸烟。[2]
中国大陆: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吸烟人口超过3亿。中国已批准FCTC,并在多个城市(如北京、上海)实施了严格的公共场所禁烟条例。然而,国家层面的全面禁烟立法进展缓慢,烟草专卖制度以及烟草利税在财政中的重要性,为烟草控制带来了独特的挑战。[45] 根据全球疾病负担研究,2020年中国男性超过20%的死亡归因于吸烟。[2]
 香港:香港自1982年起实施《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并多次修订以扩大禁烟范围。自2007年1月1日起,绝大多数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包括餐厅、办公室、学校、医院等均已全面禁烟。违规吸烟者将被处以定额罚款。[46]
香港:香港自1982年起实施《吸烟(公众卫生)条例》,并多次修订以扩大禁烟范围。自2007年1月1日起,绝大多数室内工作场所和公共场所,包括餐厅、办公室、学校、医院等均已全面禁烟。违规吸烟者将被处以定额罚款。[46]
 台湾:台湾于2009年1月11日实施《烟害防制法》修正案,规定高中以下学校、医疗机构、以及三人以上共用的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餐厅、旅馆、商场等场所可以设立独立通风的吸烟室,但多数场所选择全面禁烟。[47]
台湾:台湾于2009年1月11日实施《烟害防制法》修正案,规定高中以下学校、医疗机构、以及三人以上共用的室内工作场所全面禁烟。餐厅、旅馆、商场等场所可以设立独立通风的吸烟室,但多数场所选择全面禁烟。[47]
 美国:美国的烟草控制政策以州和地方法律为主,各州规定差异显著。许多州已实施全面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法。联邦层面,2009年通过的《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授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烟草产品进行监管,包括成分披露、广告限制和销售管制。[42]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FDA的监管步伐被批评为过于缓慢,尤其在薄荷醇禁令和新兴产品监管方面存在巨大争议。[42]
美国:美国的烟草控制政策以州和地方法律为主,各州规定差异显著。许多州已实施全面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法。联邦层面,2009年通过的《家庭吸烟预防和烟草控制法》授权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烟草产品进行监管,包括成分披露、广告限制和销售管制。[42] 尽管取得了进展,但FDA的监管步伐被批评为过于缓慢,尤其在薄荷醇禁令和新兴产品监管方面存在巨大争议。[42]
参见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