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皮浪主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皮浪主義(英語:Pyrrhonism)是哲學懷疑主義的一個學派,其拒斥教條,並倡導對所有信念的真理性懸置判斷。該學派由埃奈西德穆於公元前一世紀創立,據說其靈感源於公元前四世紀的皮浪和斐利亞修斯的第蒙的教誨。[1]
如今,皮浪主義主要通過公元二世紀末或三世紀初的作家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現存作品而為人所知。[2] 塞克斯圖斯的作品在文藝復興時期的出版,點燃了人們對懷疑主義重新燃起的興趣,並在宗教改革思想和近代早期哲學的發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歷史
皮浪主義得名於伊利斯的皮浪,他是公元前4世紀的一位希臘哲學家,後來的皮浪主義者認為他創立了第一個全面的懷疑主義思想學派。然而,關於歷史上皮浪本人的哲學信仰,古代的記載極少且常常相互矛盾:[1] 他的教誨由其學生斐利亞修斯的第蒙記錄下來,但這些作品已經失傳,僅存於後世作者引用的片段中,並基於西塞羅等後世作者的記述。提蒙所記錄的皮浪自己的哲學,可能比後來以其為名的學派要獨斷得多。[1] 儘管皮浪主義在羅馬時代早期成為懷疑主義的主導形式,但在希臘化時期,柏拉圖學院是懷疑主義的主要倡導者,直到公元前一世紀中葉,埃奈西德穆創立了作為哲學學派的皮浪主義。[3][1][4]
哲學
皮浪主義的目標是不動心,[5] 即一種靈魂不受紛擾的寧靜狀態,這種狀態源於懸置判斷——一種心靈的休憩,由於它,我們既不否定也不肯定任何事物。
皮浪主義者反駁那些獨斷論者——包括所有皮浪主義的敵對哲學——聲稱他們已找到關於「非顯見之事」的真理。他們認為,正是這些關於非顯見之事(即教條)的見解,阻礙了人獲得幸福。對於任何這類獨斷,皮浪主義者會提出正反兩方面的論證,使問題無法定論,從而懸置判斷,並由此引出心神安寧。
皮浪主義者可以細分為ephectic(從事懸置判斷者)、aporetic(從事辯駁者)[6]或zetetic(從事探求者)。[7] Ephectic(懸置判斷者)僅僅是對某一問題懸置判斷,「將感知與思想相互平衡」。[8] 這是一種較不具攻擊性的懷疑主義形式,因為有時「懸置判斷顯然只是發生在懷疑論者身上」。[9] 相比之下,辯駁者則更積極地朝目標努力,致力於反駁支持各種可能信念的論點,以達到存疑,即一種僵局或困惑的狀態,[10] 並由此導向懸置判斷。[9] 最後,探求者聲稱自己在持續探求真理,但至今未能找到,因此在繼續探求停止懸置信念的理由的同時,也繼續懸置信念。
Remove ads
儘管皮浪主義的目標是心神安寧,但它最為人熟知的是其知識論上的論證。其核心實踐是通過論證與論證的對立來進行。為協助此實踐,皮浪主義哲學家埃奈西德穆和阿格里帕發展出了一系列固定的論證形式,稱為「式」或「懸疑式」。
埃奈西德穆被認為是「埃奈西德穆十式」的創建者——儘管究竟是他發明了這些懸疑式,還是僅將其從早期的皮浪主義作品中系統化,目前尚不可知。這些懸疑式代表了懸置判斷的理由,具體如下:[11]
- 不同的動物表現出不同的感知模式;
- 類似的差異也見於不同的人類個體之間;
- 對同一個人而言,其感官所感知的信息是自相矛盾的;
- 此外,這些信息隨着身體的物理變化而時有不同;
- 再者,這些數據根據位置關係的不同而相異;
- 對象只能通過空氣、濕氣等媒介間接地被認識;
- 這些對象的顏色、溫度、大小和運動都處於永久變化的狀態;
- 所有的感知都是相對的,並且相互作用;
- 我們的印象因重複和習慣而變得不那麼敏銳;
- 所有人都在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法律和社會條件下被撫養成人。
根據塞克斯圖斯的說法,統攝這十式的是另外三式:基於判斷主體(第1、2、3、4式)、基於被判斷客體(第7、10式)、基於判斷主體與被判斷客體的結合(第5、6、8、9式)。而統攝這三式的則是關係式。[12]
Remove ads
這些「懸疑式」或「式」由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在其《皮浪主義綱要》中給出。根據塞克斯圖斯的說法,它們僅被歸於「較近的懷疑論者」,而通過第歐根尼·拉爾修,我們才將它們歸於阿格里帕。[13] 「阿格里帕五式」是:
- 異議 – 由哲學家與民眾之間的意見分歧所展示的不確定性。
- 無限後退 – 所有的證明都依賴於其自身需要證明的事物,如此以至無窮。
- 相對 – 事物隨着其關係或我們觀察它們的視角之變化而變化。
- 假設 – 所斷言的真理是基於一個未經支持的假設。
- 循環 – 所斷言的真理涉及證明的循環。
根據源於爭論的式,我們發現在日常生活中和哲學家中,對於所提出的問題都出現了無法判定的分歧。因此,我們無法選擇或排除任何東西,最終只能懸置判斷。在源於無限後退的式中,我們說,作為所提議事項的信念來源的東西,其本身需要另一個這樣的來源,而那個來源又需要另一個,如此無窮無盡,以至於我們沒有起點來建立任何東西,於是便有了懸置判斷。在源於相對性的式中,如上所述,存在的對象相對於判斷的主體和與之一同被觀察的事物,顯現為如此這般,但我們對它本質上是怎樣的懸置判斷。當我們陷入無窮後退的獨斷論者,從他們不建立,而是聲稱憑藉一種讓步而簡單地、無證明地假定的某個東西開始時,我們就有了源於假設的式。當本應用以確認所研究對象的,卻需要被所研究的對象所說服時,交互的式就發生了;於是,由於無法取其一以建立另一,我們對兩者都懸置判斷。[14]
關於這五式,第一和第三式可被視為早期埃奈西德穆十式的簡短總結。[13] 另外三式則顯示了皮浪主義體系的進展,它在感官和意見的易錯性所引出的異議之上,建立了更為抽象和形而上學的基礎。根據維克多·布羅查德的說法,「五式可被視為有史以來最徹底、最精確的懷疑主義表述。在某種意義上,它們至今仍然是不可抗拒的。」[15]
Remove ads
皮浪主義者的決策依據是他們所說的「行動標準」,即遵循表象,不帶信念,依照日常生活的常規,其基礎是:
文本
除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作品外,古代皮浪主義的文本都已失傳。有一篇由佛提烏保存的埃奈西德穆《皮浪主義論說》的摘要,以及一篇由阿里斯托克勒保存,引用皮浪的學生第蒙,關於皮浪教誨的簡短摘要,由優西比烏保存下來:
「事物本身是同樣地漠然、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因此我們的感官和我們的意見既非真亦非假。為此,我們絕不能相信它們,而應無意見、無偏見、不動搖,對每一件事物都說,它無所謂是,也無所謂不是,或者既是又不是,或者既不是也不是。」[19]
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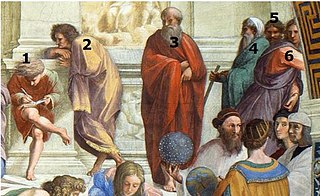
皮浪主義常與學園派懷疑主義相對照,後者是希臘化時期一種相似但有區別的哲學懷疑主義形式。[9][20] 儘管早期的學園派懷疑主義部分受到皮浪的影響,[21] 但它變得越來越獨斷,直到公元前一世紀,埃奈西德穆與學園派決裂,復興了皮浪主義,並譴責學園派為「與斯多葛派作戰的斯多葛派」。[22] 一些後來的皮浪主義者,如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甚至宣稱皮浪主義者是唯一真正的懷疑論者,將所有哲學劃分為獨斷論者、學園派和懷疑論者。[23] 獨斷論者聲稱擁有知識,學園派懷疑論者聲稱知識是不可能的,而皮浪主義者則對兩種主張都不贊同,對兩者都懸置判斷。[9][24] 二世紀的羅馬歷史學家奧盧斯·格利烏斯描述了這種區別:「……學園派(在某種意義上)領會了『什麼都不能被領會』這一事實,他們(在某種意義上)確定了『什麼都不能被確定』,而皮浪主義者則斷言,甚至連那一點似乎都不是真的,因為似乎沒有什麼是真的。」[25][20]
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還說,皮浪主義學派影響了醫學上的經驗主義學派,並與之有實質性的重疊,但皮浪主義與方法主義學派有更多共同之處,因為它「遵循現象,並從中取用似乎適宜的東西」。[26]
儘管尤利安[27]提到在他寫作時皮浪主義已經消亡,但其他作家提到了後來的皮浪主義者的存在。大約在同一時期(約公元300-320年)寫作的偽克萊門特,在他的《講道集》中提到了皮浪主義者,[28] 甚至阿加西亞斯也報道,直到公元6世紀中葉,仍有一位名叫烏拉尼烏斯的皮浪主義者。[29]
Remove ads

人們注意到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皮浪主義著作與公元2或3世紀中觀派佛教哲學家龍樹的著作之間有許多相似之處。[30] 佛教哲學家揚·韋斯特霍夫說,「龍樹關於因果關係的許多論證與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的《皮浪主義綱要》第三卷中呈現的經典懷疑論證有很強的相似性」,[31] 而托馬斯·麥克維利懷疑龍樹可能受到了傳入印度的希臘皮浪主義文本的影響。[32] 麥克維利主張皮浪主義與中觀派在佛教邏輯-認識論傳統上存在相互影響:
皮浪主義與中觀派之間一個長期以來被注意到的非凡相似之處是,在佛教中被稱為四句破(Catuṣkoṭi)的公式,而在皮浪主義形式中或可稱為四重不確定性。[33]
麥克維利還指出了皮浪主義和中觀派關於真理的觀點之間的對應關係,比較了塞克斯圖斯關於真理的兩個標準的論述[34]:一個標準用以判斷實在與非實在,另一個我們用作日常生活指南。根據第一個標準,沒有什麼是真或假的;但根據第二個標準,為了實用目的,來自感官的信息可以被認為是真或假的。如愛德華·孔策所指出,[35][查證請求] 這與中觀派的二諦說相似,即區分「勝義諦」(paramārthasatya),「對真實本來面目的無扭曲認識」,[36] 和「世俗諦」(saṃvṛti satya),「在通用語言中被約定俗成地相信的真理」。[36][37]
皮浪主義與佛教的其他相似之處包括皮浪主義格言中的一種四句破形式,以及更重要的是,懸置判斷的思想以及它如何導向平靜與解脫;皮浪主義中的心神安寧與佛教中的涅槃。[38][39]
一些學者還追溯得更遠,以確定是否有更早的印度哲學對皮浪產生過影響。第歐根尼·拉爾修關於皮浪的傳記記載,皮浪曾隨亞歷山大大帝的軍隊遊歷印度,並將他在旅途中遇到的裸體智者和術士那裡學到的東西融入了他的哲學體系。[40] 在亞歷山大征服東方期間,皮浪作為亞歷山大大帝宮廷的一員,在塔克西拉度過了大約18個月。[41] 克里斯托弗·貝克維茲[42] 在佛教的三法印和「阿里斯托克勒斯段落」中所概述的概念之間作了比較。[43]

然而,其他學者,如史蒂芬·巴切勒[44]和查爾斯·古德曼[45] 則質疑貝克維茲關於佛教對皮浪影響程度的結論。反過來,庫茲明斯基雖然對貝克維茲的觀點持批判態度,但認為皮浪受佛教影響的假說有其可信度,即使根據我們目前的信息無法確切證實。[46]
堅持徹底懷疑論的無知派可能對皮浪的影響比佛教更大。佛教徒稱無知派的信徒為Amarāvikkhepikas或「鰻魚(泥鰍)詭辯派」,因為他們拒絕信奉單一的教義。[47] 包括巴魯阿、賈亞蒂萊克和弗林托夫在內的學者認為,皮浪受到了印度懷疑主義的影響,或者至少是同意印度懷疑主義,而不是佛教或耆那教,因為他珍視心神安寧,這可以翻譯為「免於憂慮」。[48][49][50] 特別是賈亞蒂萊克,他認為皮浪可能受到了無知派前三派的影響,因為他們同樣珍視免於憂慮。[51]
Remove ads

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作品的重新發現和出版,特別是1562年由亨利·艾蒂安出版並產生廣泛影響的譯本,[52] 激發了人們對皮浪主義重新燃起的興趣。[52] 當時的哲學家們利用他的作品來尋找處理他們時代宗教問題的論據。米歇爾·德·蒙田、馬蘭·梅森和皮埃爾·伽桑狄等主要哲學家後來借鑑了塞克斯圖斯·恩丕里柯作品中概述的皮浪主義模型來構建他們自己的論證。皮浪主義的這次復興有時被視為現代哲學的開端。[52] 蒙田採用了天平的圖像作為他的格言,[53] 這也成為了皮浪主義的現代象徵。[54][55] 也有人提出,皮浪主義為勒內·笛卡爾在發展其有影響力的笛卡爾式懷疑方法,以及近代早期哲學隨之轉向知識論,提供了懷疑主義的基礎。[52] 在18世紀,大衛·休謨也深受皮浪主義的影響,並用「皮浪主義」作為「懷疑主義」的同義詞。[56][需要較佳來源]

然而,弗里德里希·尼采批評皮浪主義者的「懸置判斷者」(ephectics)是早期哲學家們的一個缺陷,他將他們刻畫為「害羞的小糊塗蛋和有羅圈腿的軟弱之徒」,容易過度沉溺於「他的懷疑衝動、他的否定衝動、他等待觀望(『懸置判斷的』)衝動、他的分析衝動、他的探索、搜尋、冒險衝動、他的比較、平衡衝動、他追求中立與客觀的意志,他追求一切「無怒無偏」的意志:我們是否已經領會到,在最長的時間裡,他們全都違背了道德與良心的首要要求?」[57]
參見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