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禁煙
政策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煙草控制(Tobacco control),常稱禁煙或控煙,是一門關注並旨在減少煙草使用的公共衛生科學、政策與實踐,目標在於降低煙草造成的發病率和死亡率。[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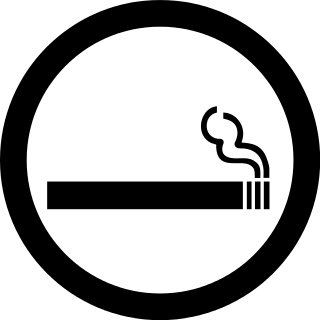
煙草控制政策涵蓋多個層面,包括立法限制在工作場所和公共場所吸煙、設立無煙環境、規範煙草產品的製造、行銷與銷售等。由於絕大多數的香煙、雪茄和水煙含有煙草,因此這些產品是煙草控制的主要對象。此外,電子煙和加熱煙等新興尼古丁產品,因其對公共衛生的潛在影響,也逐漸被納入全球煙草控制的範疇。[2]
歷史
世界上最早的禁煙令之一是1575年羅馬天主教會的一項規定,禁止在墨西哥的任何教堂內使用煙草。[3] 1590年,教宗烏爾巴諾七世採取行動,反對在教堂建築內吸煙。[4] 他威脅將任何「在教堂門廊或內部,無論是咀嚼、用煙斗吸食,還是以粉末形式從鼻子吸入」煙草的人逐出教會。[5] 教宗烏爾巴諾八世於1624年也實施了類似的限制。[6] 1604年,英王詹姆士六世及一世發表了一篇反煙論文《煙草的還擊》,其效果是提高了煙草稅。從1627年起,俄羅斯禁止煙草長達70年。[7] 鄂圖曼帝國蘇丹穆拉德四世於1633年禁止在其帝國內吸煙,並將吸煙者處決。[6]
歐洲最早的全市範圍禁煙令不久後便頒布。這類禁令於17世紀晚期在巴伐利亞、薩克森選侯國以及奧地利的某些地區實施。柏林於1723年、哥尼斯堡於1742年、斯德丁於1744年相繼禁煙。這些禁令在1848年革命中被廢除。[8] 在1865年之前,俄羅斯曾禁止在街頭吸煙。[9]
煙草控制的歷史,特別是在美國,充滿了公共衛生倡議與煙草業強大阻力之間的持續博弈。自1964年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發表第一份關於吸煙危害的報告以來,許多聯邦立法嘗試雖然表面上是公共衛生的勝利,但往往伴隨着對煙草業有利的妥協,甚至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負面後果。[10]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1965年的《聯邦香煙標示和廣告法案》(Federal Cigarette Labeling and Advertising Act)。在公共衛生倡導者的推動下,該法案要求在所有香煙包裝上標示健康警語。然而,在煙草公司的強力遊說下,法案中加入了一項關鍵的「優先適用條款」(preemption clause),禁止各州或地方政府自行立法規管煙草廣告。這項條款極大地限制了地方層級的煙草控制權力,使煙草業免於應對各地區可能出現的更嚴格廣告限制。儘管公共衛生界獲得了警示標語,但這些標語的實際效果備受質疑,反而為煙草業在日後的個人責任訴訟中提供了「消費者已被警告」的法律擋箭牌。因此,該法案被後世評價為「為煙草業利益服務的程度遠大於公共衛生」。[10]
另一項具有諷刺意味的立法是1969年的《公共衛生香煙吸煙法案》(Public Health Cigarette Smoking Act),該法案禁止在電視和廣播上播放香煙廣告。儘管這被譽為公共衛生的勝利,但它同時也終結了聯邦通信委員會的「公平原則」在煙草議題上的應用。該原則曾要求電視台播放與煙草廣告數量相當的反煙公益廣告,這些公益廣告在當時已證明能有效降低香煙消費。廣告禁令生效後,煙草業將其龐大的廣告預算轉移到平面及戶外媒體,而強有力的反煙聲音卻從廣播媒體中消失。結果,在禁令實施後的短期內,美國的香煙消費量不減反增了4.1%。[10]
煙草業在應對其他控制措施時也展現了其高超的策略。例如,雖然煙草業一貫反對提高煙稅,但當增稅法案通過時,他們會藉機將價格提升到遠高於稅收增加的幅度,並將漲價歸咎於政府,從而實現利潤的大幅增長。在1981至1985年間,美國一包香煙的平均價格上漲了36美分,其中僅11美分是新增的煙稅,而高達19.2美分則直接轉化為煙草公司的營業收入。[10] 在應對二手煙(ETS)問題上,當二手煙的危害開始動員非吸煙者支持禁煙政策時,煙草業發起了大規模的「寬容」運動,宣傳吸煙者與非吸煙者應互相尊重,並在職業安全與健康管理局(OSHA)提出室內禁煙提案時,策動了大規模信件抗議活動,成功地延宕了聯邦層級的室內空氣質素規管。[10] 此外,對於任何暗示尼古丁具有成癮性的說法,煙草業都予以激烈反擊,甚至不惜在1994年對美國廣播公司提起高達100億美元的誹謗訴訟,僅因其節目聲稱煙草公司在香煙中「摻入」尼古丁以維持成癮性。此舉產生了寒蟬效應,導致媒體在報導煙草議題時更為謹慎。[10] 這些歷史事件凸顯了煙草業在影響公共政策和輿論方面的巨大能量,也為後來的煙草控制策略提供了寶貴的教訓。
Remove ads
證據基礎

研究已產生證據,證明二手煙會導致與直接吸煙相同的問題,包括勃起功能障礙[11][12](吸煙因促進動脈粥樣硬化而導致勃起功能障礙)[13]、肺癌、心血管疾病以及肺部疾病,如肺氣腫、支氣管炎和哮喘。[14] 具體而言,統合分析顯示,終生不吸煙者若與在家吸煙的伴侶同住,其罹患肺癌的風險比與不吸煙者同住的人高出20-30%。在工作場所接觸二手煙的非吸煙者,其肺癌風險增加16-19%。[15] 由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召集、美國國家醫學院發布的一份流行病學報告指出,接觸二手煙會使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風險增加約25-30%。數據顯示,即使是低水平的暴露也存在風險,且風險隨暴露程度增加而增加。[16]
世界衛生組織轄下的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於2002年發布的一項研究結論指出,非吸煙者因煙草煙霧而暴露於與主動吸煙者相同的致癌物質。[17] 從煙草產品燃燒端釋放的側流煙[18]含有69種已知的致癌物,特別是苯並芘[19]和其他多環芳香烴,以及放射性衰變產物,如釙-210。[20] 煙草公司自己的研究已顯示,數種公認的致癌物在二手煙中的濃度高於主流煙。[21]
確認二手煙影響的科學組織包括美國國家癌症研究所[22]、美國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23]、美國國家衛生院[24]、美國公共衛生局[25]及世界衛生組織。[26]
Remove ads
對酒吧和餐廳的吸煙限制可以顯著改善這些場所的空氣質素。例如,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網站上列出的一項研究指出,紐約州的全州性法律,旨在消除封閉工作場所和公共場所的吸煙行為,大幅降低了紐約西部的餐飲服務場所的可吸入懸浮粒子(RSP)水平。在法律實施前允許吸煙的每個場所,RSP水平都有所降低,包括那些在基線時僅觀察到來自相鄰房間煙霧的場所。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結論是,他們的結果與其他研究相似,這些研究也顯示在實施禁煙令後,室內空氣質素得到顯著改善。[27]
2004年的一項研究顯示,紐澤西州的酒吧和餐廳的室內空氣污染水平是鄰近的紐約市的九倍以上,而紐約市當時已經實施了禁煙令。[28]
研究還表明,改善的空氣質素轉化為員工接觸到的毒素減少。[29] 例如,在實施吸煙限制的挪威場所的員工中,測試顯示吸煙和非吸煙工人的尿液中尼古丁水平均有下降(與實施無煙政策前相比)。[30]
2009年,美國羅伯特·伍德·約翰遜基金會的全國性項目辦公室「公共衛生法律研究計劃」發布了一份證據摘要,總結了評估特定法律或政策對公共衛生影響的研究。他們指出:「有強有力的證據支持禁煙令和限制措施是旨在減少二手煙暴露的有效公共衛生干預措施。」[31]
許多吸煙者隨意丟棄煙蒂,這些煙蒂很容易進入生態系統。煙蒂含有高濃度的尼古丁,對大多數動物來說是一種致命的毒素。許多動物,包括嬰幼兒,可能會攝入這些煙蒂,面臨尼古丁中毒的直接威脅以及攝入塑膠的相關危險。此外,燃燒的煙蒂可能引發野火。將煙蒂丟入下水道會導致排水管堵塞和隨後的洪水。[32]
煙草種植也對環境產生負面影響。首先,它導致森林砍伐,全球約5%的森林砍伐與煙草種植有關。據估計,每生產300支香煙就會損失一棵樹。森林砍伐導致氣候變遷、生物多樣性喪失、土壤侵蝕和水污染。其次,煙草種植需要大量肥料,導致土壤退化和污染。一些肥料甚至含有放射性物質,這些物質可能轉移到吸煙者和接觸二手煙者的肺部。此外,煙草種植消耗大量水資源,加劇了水資源短缺。過度使用殺蟲劑會污染水源、傷害野生動物,並對煙農構成健康風險,尤其是在發展中國家,那裏可能缺乏安全知識且童工現象普遍。煙草生產還釋放大量溫室氣體,加劇氣候變遷。煙草廢棄物污染海洋、河流、土壤和城市環境。在發展中國家,煙草種植引發了糧食安全問題,因為寶貴的水和農田被用於種植煙草而非糧食作物。總體而言,煙草種植對環境和人類健康都造成嚴重損害,有必要採取措施減少其負面影響。[33]
Remove ads
全球框架公約與MPOWER策略
為應對全球煙草流行,各國在《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指導下,已實施了一系列被證明行之有效的政策。世界衛生組織(WHO)為協助各國加速推動煙草控制,將其中六項基於證據的核心措施整合為MPOWER政策包。這六項策略相輔相成,當全面實施時能發揮最大效果,共同營造一個不利於煙草消費的社會環境。[2]
提高煙草產品的稅率與價格,被公認為是降低煙草消費最有效且成本效益最高的單一干預措施。[1] 經濟學研究一致顯示,煙價與消費量之間存在明確的負相關。一般而言,煙價每提高10%,在高收入國家可降低約4%的吸煙率,在中低收入國家則效果更為顯著。[34] 高煙價能有效阻止青少年開始吸煙,並促使經濟能力較弱的吸煙者戒煙或減少吸煙量。一個顯著的實例是菲律賓於2012年推行的「罪惡稅改革」(Sin Tax Reform),該政策大幅提高煙草和酒精稅,不僅成功降低了吸煙率,更將增加的稅收專門用於資助全民健康保險,實現了公共衛生與財政收入的雙贏。[35] 澳洲和英國等國也長期透過維持高煙稅政策,取得了顯著的吸煙率下降。[1] 儘管證據充分,但煙草稅仍是MPOWER措施中,在全球範圍內達到最佳實踐水平最低的政策之一。[2]
制定並執行全面的無煙法律,禁止在室內公共場所、工作場所及公共交通工具中吸煙,是保護非吸煙者免受二手煙危害的根本措施。科學證據表明,二手煙並無安全暴露水平,即使短暫接觸也會對健康造成危害。例如,愛爾蘭於2004年成為全球首個實施全國性工作場所(包括酒吧和餐廳)禁煙的國家。政策實施後,不僅酒吧員工的呼吸系統健康狀況顯著改善,國家的心血管疾病住院率也隨之下降,同時對餐飲業的整體經濟並未造成負面影響。[10]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普韋布洛市在實施禁煙令後的18個月內,心臟病發作住院率下降了27%。[36]

為吸煙者提供戒煙支持,是煙草控制策略中幫助個體擺脫成癮的關鍵一環。有效的戒煙服務體系應包括由醫療專業人員提供的簡短建議、戒煙熱線、行為諮詢以及藥物治療,如尼古丁替代療法的尼古丁貼片、尼古丁咀嚼錠等。研究顯示,使用NRT可以將戒煙成功率提高一倍。[10] 以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為例,其提供全面的免費戒煙服務,包括一對一諮詢、團體支持和處方戒煙藥物,成為全球戒煙服務的典範。為提高可及性,許多國家如美國已將NRT產品轉為非處方藥,使吸煙者能更便捷地獲取。[10] 美國《臨床實踐指南》(Clinical Practice Guideline)也強調,醫護人員應在每次就診時主動詢問患者的吸煙狀況並提供戒煙建議。[37]
透過煙品包裝直接向消費者傳達煙草的健康風險,是一種高效率、廣覆蓋的宣傳方式。採用大面積、醒目的圖文健康警示,能有效打破煙草業透過精美包裝營造的品牌形象,增加吸煙者對健康危害的認知,並激發其戒煙動機。[1] 更進一步的措施是推行簡易煙盒計劃,即統一煙盒的顏色、字體,並禁止使用品牌標誌,僅保留標準化的品牌名稱和健康警示。例如,加拿大是全球最早採用大幅圖文警示的國家之一,其經驗證明這項措施能有效提升公眾對吸煙風險的了解。[1] 澳洲在2012年率先實施素面煙品包裝法案,研究顯示該政策成功降低了煙盒的吸引力,減少了品牌對消費者的誤導,並強化了健康警示的效果。[1] 目前,圖文警示是MPOWER措施中覆蓋人口最廣的政策之一。[2]

全面禁止所有形式的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對於防止煙草業誤導公眾、吸引新使用者(特別是年輕人)至關重要。這不僅包括傳統媒體(如報紙、電視)的廣告,也涵蓋銷售點的陳列、品牌商品、體育文化活動贊助以及網絡行銷等間接宣傳手段。研究指出,全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的禁令能使吸煙率下降約7%,在某些國家甚至更高。[2] 歷史經驗提供了重要的教訓。例如,美國在1971年禁止了廣播電視煙草廣告後,煙草業迅速將龐大的行銷預算轉移至平面媒體、戶外看板和體育贊助,導致煙草消費量在短期內甚至出現反彈。[10] 這凸顯了唯有「全面」禁止所有行銷渠道,才能有效遏制煙草業的影響力。儘管此措施效益顯著,但在全球範圍內,尤其在高收入國家,其執行率仍然偏低。[2]
建立持續、系統的監測機制,是制定、評估和改進煙草控制政策的基礎。透過全國性的調查,可以追蹤煙草使用(包括各類產品)的流行率、相關的健康與經濟負擔,以及各項干預措施的成效。高品質的數據有助於識別高風險人群,並為政策調整提供科學依據。具體實例包括美國的「煙草與健康人口評估」(PATH)研究,這是一項大型全國性縱貫性研究,旨在長期追蹤煙草使用行為及其健康影響,為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的煙草監管決策提供重要數據。[38] 在國際層面,「國際煙草控制政策評估項目」(ITC Project)在超過29個國家進行,旨在評估《煙草控制框架公約》各項政策在不同國家的實施效果,為全球煙草控制提供了寶貴的跨國比較數據。[38]
公共衛生影響與成效
全球範圍內的煙草控制努力已取得顯著成效。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數據,全球15歲以上人群的吸煙率已從2000年的27%下降至2022年的約20.9%。據估算,若無這些政策干預,目前的吸煙者人數將會多出3億。[2] 實施全面煙草控制政策的國家,其吸煙率均出現明顯下降。例如,巴西在推行包括廣告禁令、圖文警示和高稅率在內的綜合政策後,成人吸煙率從1989年的34.8%降至2019年的12.6%,估計避免了數十萬人因煙草相關疾病死亡。[1] 禁煙令的實施也能立即帶來公共衛生效益,多個國家和地區的研究發現,在實施公共場所禁煙後,因急性心肌梗塞和哮喘等疾病的住院率顯著下降。[39]
除了健康效益,煙草控制還帶來了可觀的經濟效益。它不僅能節省大量因治療煙草相關疾病而產生的醫療開支,還能通過改善勞動力健康狀況來提升社會生產力。世界銀行的研究指出,投資於煙草控制的每一美元,平均可帶來數十美元的經濟回報。[1] 更深遠的影響在於社會規範的轉變。持續的煙草控制努力有助於「去正常化」(denormalization)吸煙行為,改變社會對吸煙的接受度,使其不再被視為一種正常的社交行為。這種文化上的轉變對於預防青少年接觸和開始吸煙尤為重要。[40]
挑戰、爭議與批評
儘管煙草控制取得了巨大進展,但仍面臨諸多挑戰和批評。
煙草業及其利益相關者是煙草控制政策推進的最大阻力。[2] 他們採取的策略包括:透過政治遊說、競選捐款等方式影響立法,或對已頒布的禁煙法規提起訴訟,以延遲或削弱政策實施。[10] 煙草業還會資助或進行有利於己的「科學研究」,質疑二手煙危害的證據,或誇大禁煙政策對經濟的負面影響。[2] 此外,他們也透過贊助體育、文化活動或推出環保項目等「企業社會責任」偽裝,塑造正面形象,以轉移公眾對其產品危害的注意力。[41] 為應對此問題,《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第5.3條明確要求締約方保護其公共衛生政策不受煙草業商業及其他既得利益的影響。

電子煙、加熱煙等新興產品的普及為煙草控制帶來了新的複雜性。支持者認為這些產品可作為傳統香煙的減害替代品,但反對者擔心其對青少年的吸引力,可能導致尼古丁成癮,並成為吸食傳統香煙的「入門磚」(gateway effect)。[2] 這些產品的長期健康影響尚不完全清楚,其產生的氣霧也並非無害。[2] 此外,監管也面臨困境。例如,美國FDA在《煙草控制法案》實施後的十年中,其對電子煙的「上市前審查」(premarket review)流程被批評為本末倒置,客觀上助長了青少年電子煙的流行。[42] 追蹤這些產品的使用模式也極具挑戰,需要如PATH研究這樣的大型縱貫性數據來理解使用者在不同產品(單獨使用或多重使用)之間的轉換行為。[38]
許多國家,特別是中低收入國家,雖然制定了禁煙法律,但因資金不足、執法能力薄弱、公眾意識不高等原因,導致政策執行不力,效果大打折扣。[1] 在美國等已建立監管框架的國家,挑戰則更多體現在監管機構的「政治意願」上。批評者認為,FDA在煙草控制上時常表現出過度謹慎甚至癱瘓,而非採取大膽果斷的行動,導致許多關鍵政策(如薄荷醇禁令)被長期擱置。[42] 這種「緩慢的步伐」使得煙草業有充分的時間來應對和破壞監管措施。
部分反對者認為,禁煙政策過度干預了個人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私有財產所有者的經營權。然而,主流公共衛生觀點認為,當個人行為(如吸煙)對他人健康構成威脅時,公共利益應優先於個人自由。[43] 關於經濟損失的擔憂,儘管部分餐飲和娛樂業者擔心禁煙會導致顧客流失,但大量獨立研究表明,禁煙令對這些行業的整體經濟影響通常是中性或正面的,因為無煙環境會吸引更多非吸煙顧客和家庭消費。[44]
煙草控制政策在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影響存在差異,這引發了對健康公平的深切關注。例如,提高煙稅雖能有效降低總體吸煙率,但可能加重低收入成癮者的經濟負擔。因此,政策制定需要輔以針對弱勢群體的戒煙支持和補助措施,以確保煙草控制的益處能惠及所有人。[42] 更為嚴峻的是,煙草業常針對特定族群進行掠奪性行銷,造成了嚴重的健康不平等。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美國煙草業幾十年來針對非裔美國人社區進行薄荷醇香煙的精準行銷。然而,2009年美國《煙草控制法案》在禁止調味煙的同時,卻給薄荷醇開了一個「可恥的例外」。這一妥協被批評為「立法的代價往往由最無力負擔的人——那些被不成比例影響、權力最小的群體——來支付」,是煙草控制中亟待解決的社會正義問題。[42]
各國/地區狀況
全球已有183個締約方批准了《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但各國的執行進度和成效參差不齊。[2] 根據煙草流行的發展,各國大致可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為流行初期(男性吸煙率<15%);第二階段為流行上升期;第三階段為流行高峰或初步下降期;第四階段為流行大幅下降期(吸煙率<25%)。[2] 許多非洲和中東國家的男性吸煙流行仍處於上升期,而歐洲、東亞和北美大部分地區則處於第三或第四階段。女性的煙草流行通常比男性晚數十年,在許多地區仍處於初期階段,這也為預防工作提供了機會之窗。[2]
MPOWER各項措施的全球實施水平也極不均衡。截至2024年,圖文健康警示是覆蓋人口最廣的措施,而煙草稅則是實施程度最低的最佳實踐措施之一。全面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TAPS)在中低收入國家的採納率甚至高於高收入國家。[2] 儘管取得了進展,但全球仍有近20億人未受到任何一項最高標準的MPOWER措施保護,顯示出全球煙草控制工作的巨大差距。[2]
 中國大陸: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煙草生產國和消費國,吸煙人口超過3億。中國已批准FCTC,並在多個城市(如北京、上海)實施了嚴格的公共場所禁煙條例。然而,國家層面的全面禁煙立法進展緩慢,煙草專賣制度以及煙草利稅在財政中的重要性,為煙草控制帶來了獨特的挑戰。[45] 根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20年中國男性超過20%的死亡歸因於吸煙。[2]
中國大陸: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煙草生產國和消費國,吸煙人口超過3億。中國已批准FCTC,並在多個城市(如北京、上海)實施了嚴格的公共場所禁煙條例。然而,國家層面的全面禁煙立法進展緩慢,煙草專賣制度以及煙草利稅在財政中的重要性,為煙草控制帶來了獨特的挑戰。[45] 根據全球疾病負擔研究,2020年中國男性超過20%的死亡歸因於吸煙。[2]
 香港:香港自1982年起實施《吸煙(公眾衞生)條例》,並多次修訂以擴大禁煙範圍。自2007年1月1日起,絕大多數室內工作場所和公共場所,包括餐廳、辦公室、學校、醫院等均已全面禁煙。違規吸煙者將被處以定額罰款。[46]
香港:香港自1982年起實施《吸煙(公眾衞生)條例》,並多次修訂以擴大禁煙範圍。自2007年1月1日起,絕大多數室內工作場所和公共場所,包括餐廳、辦公室、學校、醫院等均已全面禁煙。違規吸煙者將被處以定額罰款。[46]
 臺灣:台灣於2009年1月11日實施《煙害防制法》修正案,規定高中以下學校、醫療機構、以及三人以上共用的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煙。餐廳、旅館、商場等場所可以設立獨立通風的吸煙室,但多數場所選擇全面禁煙。[47]
臺灣:台灣於2009年1月11日實施《煙害防制法》修正案,規定高中以下學校、醫療機構、以及三人以上共用的室內工作場所全面禁煙。餐廳、旅館、商場等場所可以設立獨立通風的吸煙室,但多數場所選擇全面禁煙。[47]
 美國:美國的煙草控制政策以州和地方法律為主,各州規定差異顯著。許多州已實施全面的室內公共場所禁煙法。聯邦層面,2009年通過的《家庭吸煙預防和煙草控制法》授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煙草產品進行監管,包括成分披露、廣告限制和銷售管制。[42] 儘管取得了進展,但FDA的監管步伐被批評為過於緩慢,尤其在薄荷醇禁令和新興產品監管方面存在巨大爭議。[42]
美國:美國的煙草控制政策以州和地方法律為主,各州規定差異顯著。許多州已實施全面的室內公共場所禁煙法。聯邦層面,2009年通過的《家庭吸煙預防和煙草控制法》授權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對煙草產品進行監管,包括成分披露、廣告限制和銷售管制。[42] 儘管取得了進展,但FDA的監管步伐被批評為過於緩慢,尤其在薄荷醇禁令和新興產品監管方面存在巨大爭議。[42]
參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