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蘇聯控制論史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控制論在蘇聯有其自身獨有的特點,這是因為控制論的研究和蘇聯意識形態及國內政治經濟局勢變化有所關聯。20世紀50年代初,由於反美意識形態,蘇聯官方對諾伯特·維納所提出的控制論加以激烈批評;而史太林逝世後,控制論研究轉向合法,並逐漸在蘇聯學術界活躍起來,到60年代成為一門顯學,寫入蘇共黨綱,成為意識形態術語,並就此得到各界追捧;最終,在20世紀70年代至80年代走向式微。
起初在1950年至1954年,蘇聯當局對控制理論持完全負面的態度,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號召社會各界加大反美批判力度,報界瞄準美國數學家維納提出的控制論,將之批判成「反動偽科學」「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完全體現」,撰文批判嘲諷。史太林逝世後,尼基塔·赫魯曉夫推動政治和文化解凍,當局對控制論的態度就此逆轉,控制論研究正常化,成為一門「嚴肅、重要的科學」,《哲學問題》期刊在1955年刊文介紹控制理論。一批先前遭官方抑制的科學研究,如結構語言學、孟德爾遺傳學,也都被歸類為「控制論」,並成立「控制論委員會」,資助這些新領域的研究,主席為阿克塞爾·別爾格院士。
到20世紀60年代,蘇聯控制論研究可謂蔚然成風,「控制論」在蘇聯學術界成為時髦字眼,也有學者批評別爾格志在學術政治,欲領導其委員會「涵蓋蘇聯一切科研工作」。到80年代,控制論研究走向式微,其意識形態涵義逐步被「信息學」取代。
Remove ads
史太林時代的批判(1950–1954)
控制論:二戰後出現在美國,也傳播至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偽科學。控制論鮮明地表現出資產階級世界觀的幾個基本特徵——毫無人性,力圖把勞動人民變成機械的附屬品,變成生產工具和戰爭工具。與此同時,控制論也體現了一種帝國主義烏托邦的特質——在工業和戰爭領域,用一台機器取代有生命力、會思考、為自身利益奮鬥的人。新一次世界大戰的煽動者們將控制論運用到他們骯髒的實際行動中。
1954年《簡明哲學詞典》「控制論」詞條[1]
蘇聯官方媒體和學術機構最初對控制論的看法是完全負面的。20世紀50年代初,為應對北約組織成立,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號召社會各界加大反美批判力度,要「展現資產階級文化和道德的腐敗,戳穿美國宣傳機器的神話[2]」,各大報刊因此需就西方世界的各個領域以各種角度展開批判[3][4]。
最初向控制理論發難的記者是鮑里斯·阿加波夫。美國計算機科學研究在戰後不斷發展,1950年1月23日《時代》雜誌在封面刊登了一幅漫畫,畫中是一台哈佛馬克三號計算機,配以標語「人類能造出超人嗎?」1950年5月4日,阿加波夫在《文學報》刊載《馬克三號:一台計算器》一文,在文中嘲諷美國人熱衷於這些新型「思考機器」,做着將這些機器投入軍事和工業用途的美夢。他還在文中批判控制理論創始人諾伯特·維納,稱他是「資本主義用來替代真正科學家的反啟蒙主義者和鼓動家」的典型代表,稱美國對計算機的宣傳是「一場蒙蔽大眾的運動」[3][4][5]。
儘管阿加波夫撰文的行為並非是受任何官方機構委託,也從未提及「控制論」一詞,但阿加波夫的文章很快就被公眾視為官方批判控制理論的一個信號。圖書館流通名錄將維納所著之《控制論》撤下,各大報刊紛紛效仿,把控制論斥為反動偽科學。哲學研究所學者米哈伊爾·雅羅舍夫斯基發起針對「語義唯心主義[a]」哲學的公開批判,將維納及其提出的整個控制理論定性為語義唯心主義這種「反動哲學」的一部分。1952年,《文學報》又刊登了一篇更加明確反控制論的文章,徹底拉開批判運動的序幕,隨後一系列報章都撰文對控制論展開口誅筆伐[4][8][9]。在這場批判運動的高峰期,1953年10月,官方哲學刊物《哲學問題》發表了一篇題為《控制論為誰服務?》、署名「唯物主義者」的文章。該文譴責控制論是一種「反人道的偽理論」,本質是「正滑向唯心主義的機械論」,並直指美國軍方就是「控制論所服務的神」[10][11][12][13]。
在這段時期,蘇聯最高領導人史太林本人從未參與到批判控制論的行列當中。蘇聯科學部部長尤里·日丹諾夫回憶稱「史太林從未反對過控制論」,還不遺餘力「推進計算機技術」,以期讓蘇聯取得技術優勢[14]。雖然這場運動的規模並不大,僅有10篇左右的批判文章問世,但當代學者瓦列里·希洛夫認為,這一系列批判即構成了中央意識形態機構的「嚴格行動指令」,即宣告控制論是應被批判和消滅的資產階級偽科學[13]。
這些批判者中很少有人接觸過控制論的原始文獻,阿加波夫的消息來源僅限於1950年1月那期《時代》雜誌;研究所的批評依據是1949年的《ETC:普通語義學評論》期刊;在所有批判文章中,只有《哲學問題》署名「唯物主義者」的文章直接引用了維納的《控制論》[15][16]。他們揀選維納言論中聳人聽聞的部分,或者基於其他蘇聯同類主題書籍去臆測,將維納描繪成一個唯心主義者、機械主義者,批判他「將科學和社會學思想簡化為單純的機械模型」[17]。文章引用維納對第二次工業革命和「無需人力參與的流水線」所作的悲觀推測,據此為他貼上「專家統治論者」的標籤,說他希望看到「全由計算機大腦控制的機器完成,沒有工人的生產過程」,「既沒有罷工或罷工運動,更不會有革命起義」[18][19]。當代學者格羅維奇如此概括這一時期的批判:「每個人都上綱上線,逐步誇大控制論的意義,直至它被視作帝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完整化身」[10]。
Remove ads
合法化及興起(1954–19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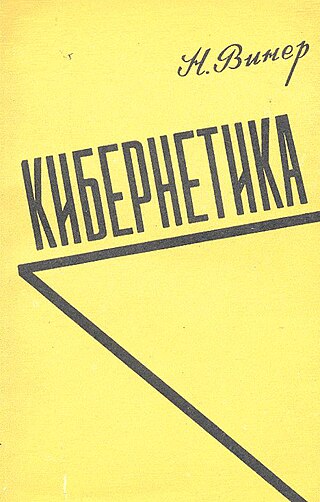
1954年史太林逝世,隨後蘇聯最高領導人赫魯曉夫在各領域推進改革,控制論得以擺脫先前背負的意識形態罵名,逐步在公眾視野中恢復聲譽。蘇聯學者也將控制論視為逃離史太林主義意識形態的一條新道路,藉此重新提倡起控制論所代表的數學客觀性[21][22][23]。在赫魯曉夫時期,控制論不僅成為一門合法的科學,而且成為了蘇聯學術界的熱門領域[24][25]。
軍事計算機科學家阿納托利·基托夫上校回憶道,他在國家機械設備部特種製造局的機密圖書館碰巧發現《控制論》一書,並意識到,控制論並非如當時官方報章所認為的那樣,是資產階級偽科學,而恰恰相反,是一門嚴肅而重要的科學。他與數學家阿列克謝·李亞普諾夫一同於1952年向《哲學問題》投遞了一篇支持控制論的文章。《哲》並未明確反對,不過要求李亞普諾夫和基托夫在文章發表前公開講授控制論。從1954年到1955年,他們共舉辦121場控制理論研討會[26][27][28]。哲學及意識形態學者恩斯特·科爾曼也加入這場平反行動。1954年11月,科爾曼在社會科學院演講,譴責壓制控制論研究。他還赴《哲學問題》辦公室,要求將他的演講稿發表出來[29]。
1955年,《哲學問題》刊載兩篇文章,一篇是《控制論的主要特徵》,由謝爾蓋·索博列夫、阿列克謝·李亞普諾夫、阿納托利·基托夫聯合撰寫;另一篇是恩斯特·科爾曼撰寫的《什麼是控制論?》。這成為蘇聯控制論研究興起的首個信號,為控制論此後在蘇聯的發展奠定了基礎[16]。
在《控制論的主要特徵》中,三位學者試圖將控制論闡釋為一個連貫的科學理論,並將之適當改造以便應用於蘇聯。他們也刻意避免哲學和意識形態探討,並將維納描述成美國的一位反資本主義學者。他們主張,控制論的基本原理如下:信息論;自動高速電子計算機理論,即與人類思維過程相似的自組織的邏輯過程的理論;自動控制系統理論,主要是反饋理論[30][31][32]。科爾曼在《什麼是控制論?》中提出了一套控制論的歷史脈絡,稱其源自於蘇聯,並糾正往年批判言論中的偏誤,他在辯證唯物主義框架內引用術語作出論述,批判這些反對者犯了唯心主義和生命主義錯誤[33][34]。
控制論在蘇聯由此轉向合法化。時任國防部副部長阿克塞爾·別爾格院士撰寫了數篇秘密報告,痛陳蘇聯信息科學發展狀況堪憂,認為學界對控制論的打壓是罪魁禍首。1956年6月,黨內批准派出一支小組代表蘇聯參加第一屆國際控制論大會,代表團隨後在匯報中稱蘇聯在計算機科技領域落後於發達國家[35]。此後,官方出版物中關於控制論的負面定義就此消失。1958年,維納著作《控制論》和《人有人的用處》首版俄文譯本正式出版[36]。同年,蘇聯首個控制論期刊《控制論問題》(Проблемы кибернетики)創刊,由李亞普諾夫擔任主編[37]。
記者問:在您上次蘇聯之行中,您發現蘇聯人很重視計算機嗎?
維納答:我來告訴你他們有多重視。他們在莫斯科有一家研究所,在基輔有一家,在列寧格勒有一家,在埃里溫、第比利斯、撒馬爾罕、塔什干和新西伯利亞也各有一家。可能還有其他地方。
記者問: 他們是否像我們一樣,在充分利用這門科學?
維納採訪實錄,於1964年發表[38]
為了籌備宣傳1960年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首屆大會,維納親赴蘇聯,在莫斯科綜合技術博物館就控制論發表演講。他抵達後發現演講廳現場非常熱鬧,到場學者們將演講廳擠得水泄不通,甚至有些人坐在過道和樓梯上,其中還包括昔日反控制論的多家媒體記者,包括《哲學問題》在內,以求採訪維納[39]。維納本人也對美國記者介紹了蘇聯人對控制論研究的巨大熱情[38]。
1959年4月10日,別爾格院士向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提交報告,要求成立組織專門推進控制論研究,由李亞普諾夫所撰寫。主席團於是決定成立控制論委員會,由別爾格擔任主席,李亞普諾夫擔任副主席[24][40]。該委員會的覆蓋範圍極廣,截至1967年,其下涵蓋多達15個學科領域,從語言學到法學均有涉獵,並以「控制論語言學」「法律控制論」稱之。在赫魯曉夫對科研採取寬鬆政策的時期,控制論委員會實質上是一個傘式組織,許多曾受壓制的學科都囊括在其中,包括:非巴甫洛夫生理學(「生理控制論」)、結構語言學(「控制論語言學」)以及孟德爾遺傳學(「生物控制論」)等[41][42]。
李亞普諾夫還推動成立了一個20人的控制論系,致力於為控制論研究爭取官方經費。即便如此,李亞普諾夫仍遺憾表示「我國控制論領域缺乏組織」。1961年6月,結構語言學家推動成立了符號學研究所,由小安德烈·馬爾可夫擔任所長。李亞普諾夫因此又和結構語言學家合作推動設立控制論研究所,但未獲赫魯曉夫批准。退而求其次,控制論委員會被授予研究機構級別的職能,但並未擴充編制[43]。
Remove ads
巔峰及式微(1961–1980年代)

進入20世紀60年代,控制論在蘇聯學界成為一門顯學。別爾格領導的控制論委員會出資在媒體宣傳控制論,贊助製作廣播節目,名為《生活中的控制論》,時長20分鐘;為莫斯科電視台贊助一系列介紹計算機技術進步的節目;還面向各級幹部、工人舉辦了數百場控制論講座。1961年,委員會出版官方文集《控制論——為共產主義服務》,將控制論定性為一門社會主義科學[44]。
在蘇共二十二大上,蘇共宣布控制論是「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主要工具」,赫魯曉夫稱發展控制論是蘇聯科學勢在必行的任務[24][45],將「控制論」寫入黨綱:「在工業、建築工業和運輸業的生產過程中,在科學研究中,在計劃計算和設計計算中,在核算和管理方面,將廣泛地應用控制論、電子計算機和操縱裝置。」控制論成為學術界的一門風尚,甚至在追求事業發展的學者中間成為一個流行語。參與控制論研究的學者規模迅速擴大[46]。美國中情局報告稱,1962年7月的「控制論哲學問題會議」吸引了「約1000名專家,包括數學家、哲學家、物理學家、經濟學家、心理學家、生物學家、工程師、語言學家和醫生[47]」。美國情報機構被這股熱潮誤導,誤將體制內的熱情視同科研投入,總統特別顧問小亞瑟·施萊辛格警告總統約翰·甘迺迪稱,蘇聯大加投入控制論研究,在技術與經濟生產效率上獲得「巨大優勢」,若美國缺乏相應計劃,「我們就完蛋了」[48]。
1962年7月,別爾格提出調整控制論委員會的組織職能,意圖覆蓋到蘇聯科學的各個研究領域。這個計劃在委員會內部遭到反對,有專家在給李亞普諾夫的信函中抱怨:「委員會幾乎毫無成果,別爾格只要紙上功夫,一味追求擴張。」利亞普諾夫感到不滿,認為控制論研究的方向有所偏離,他拒絕為《控制論——為共產主義服務》撰稿,隨後逐漸淡出控制論界。有回憶錄寫道,利亞普諾夫退出學界,意味着「統一控制論研究的中心消失了,控制論研究自會四分五裂[49]。」儘管老一輩控制論學者多有抱怨,但在這一時期,蘇聯控制論研究整體呈現出爆發式增長:1962年,控制論委員會領導170個項目、29家機構,到1967年,擴張至500個項目、150家機構。[50]
控制論所代表的計算理性符合蘇共官方的計劃經濟自動化的建設願景,所以在意識形態話語上獲得成功,同時,基於50年代起就投入研發的計算機系統,也開發出諸多應用成果,並在國民經濟領域中推廣應用,如工業控制系統、數值控制系統、自動化過程控制系統、航空預訂系統、售票自動系統、交通信號控制系統、天氣預報計算系統、疫情傳播計算機建模[51][52]等。1970年,莫斯科國立大學設立計算數學與控制論學院,1971年,又成立計算工具科學委員會[53]。70年代後期,計算機科學開始引入莫斯科中小學教育[54]。
1962年,格盧什科夫帶頭組建烏克蘭科學院控制論研究院,擔任院長。格盧什科夫在控制理論領域作出開創性貢獻,被後世譽為蘇聯控制學與信息技術之父,並在1973年為《大英百科全書》的「控制論」詞條撰文,發起並擔任《控制論百科全書》主編[55]。他將控制論定義為一門綜合性的科學,研究人與機器之間的有效交互,提出了「眼睛和手」「自動閱讀機」「自組織結構」等概念,為人工智能奠定了基礎。他將自動機理論引入計算機構造學,並帶頭研製出多款大型計算機和程式語言,成為現代計算機設計的先驅。
然而,在更宏大的計算機網絡建設上,控制論專家卻遇到困境。阿納托利·基托夫在1962年提出建立統一國家計算中心網絡,希望建立計算機網絡,用於改善經濟計劃制定;同年,格盧什科夫提出以莫斯科為中心建立三級網絡結構,命名其為全國計算和信息處理自動化系統(OGAS)。這些計算機利用電信設施通信,同時各終端間也可互相通信[56]。這兩項計劃均被相關單位駁回而未能付諸實踐,各個官僚機構並不願意放棄手中原有的資源和權力而與其他部門共享。相比之下,美國ARPANET則是於1969年投入運行。1978年,建成全聯盟學術網絡,通過計算機為蘇聯各地科研機構和民間機構提供數字連接,成為蘇聯互聯網的前身。
「控制論運動」在20世紀70年代初起逐步式微。當代學者格羅維奇認為,在當時,蘇聯學界紛紛向控制論靠攏,於是故意引入控制論概念和行話,作學術投機,這導致控制論運動逐漸失去了往日鋒芒,最初一批學者以控制理論改造學界的目標就此被掩蓋了[57]。昔日各個陷入爭議的西方理論和學科,一度依賴控制論熱潮作為保護傘,後來逐步成為科學主流,而控制論在蘇聯淪為鬆散而不連貫的意識形態拼湊物[41]。有部分學者自覺被排擠,於是選擇移民,包括瓦倫丁·圖爾欽、亞歷山大·勒納、伊戈爾·梅爾丘克[58]。到20世紀80年代,控制論在蘇聯式微,學界轉而追捧起「信息學」概念[41]。
Remove ads
著名學者
- 阿克塞爾·別爾格
- 維克托·格盧什科夫
- 阿納托利·基托夫
- 安德烈·柯爾莫哥洛夫[59]
- 列昂尼德·克萊斯默
- 阿列克謝·李亞普諾夫
- 謝爾蓋·索伯列夫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書目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