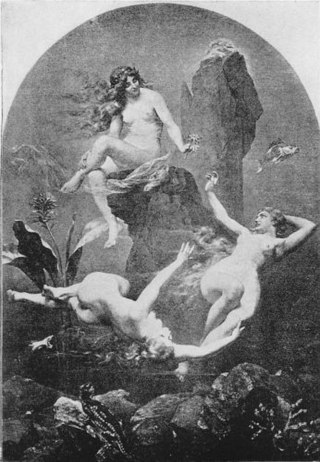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萊茵少女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萊茵少女(Rhinemaidens)[a]是出現在德國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納歌劇系列《尼伯龍根的指環》中的三位水仙女(Rheintöchter 或「萊茵女兒」)。她們的名字分別是沃格琳德(Woglinde)[b]、韋爾貢德(Wellgunde)[c]和弗洛希爾德(Flosshilde或Floßhilde)[d]。儘管她們通常被視為一個整體,但卻是《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登場的34個角色中唯一沒有源自古挪威語《詩體埃達》的角色。瓦格納的創作靈感來自其他傳說與神話,尤其是《尼伯龍根之歌》中提及的多瑙河水精靈或美人魚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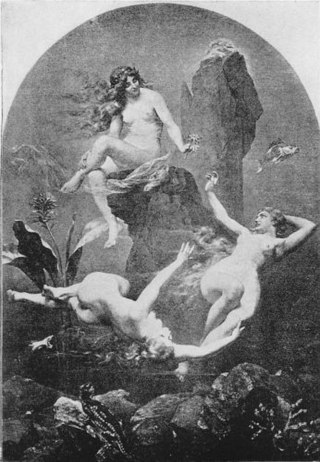
萊茵少女在《尼伯龍根指環》系列歌劇中承載的核心概念——她們對萊茵黃金的守護不力,以及竊取黃金並將其轉化為攫取世界權力之利器的條件(即放棄愛情)——完全出自瓦格納的原創構思,這些元素不僅是整個戲劇的起點,更是推動劇情發展的核心動力。
萊茵少女是四聯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中首位與末位登場的角色群體,她們既出現在首部劇《萊茵的黃金》的開幕場景中,也在終章《諸神的黃昏》的高潮時刻從萊茵河水中升起,從布倫希爾德的骨灰中奪回指環。儘管被描述為道德上純真無邪的存在,但她們卻展現出複雜的情感層次,某些表現甚至與天真相去甚遠。她們充滿誘惑力且難以捉摸,與其他角色毫無關聯,其起源亦未被明確交代,僅偶爾提及一位未明確定義的「父親」。
與萊茵少女相關的各種音樂主題被認為是整個《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中最具抒情性的存在,為宏大的敍事注入了難得的舒緩與魅力。這些音樂不僅包含重要的旋律與樂句,還在歌劇其他部分通過變奏與發展,用以刻畫其他人物與情境,並將情節推進與故事源頭相聯結。
Remove ads
起源
萊茵少女是《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中唯一不是源自冰島史詩《詩體埃達》或《散文埃達》的角色[3]。水仙女或者是水精靈(德語:Nixen)廣泛存在於歐洲各地的神話傳說中,通常(但非絕對)是以帶有偽裝的反面形象出現[4]。瓦格納在構建《尼伯龍根的指環》敍事時,大量且靈活地借鑑了這些傳說,其筆下的萊茵少女很可能源自德國史詩《尼伯龍根之歌》[4]。在該史詩的某一情節中,哈根(Hagen)與龔特爾偶遇幾位在多瑙河中沐浴的美人魚或水精靈(中古高地德語:merwîp[5];現代德語:Meerweib)。哈根偷走了她們的衣物,為索回衣物,名為哈德堡(Hadeburg)的美人魚給出虛假的預言稱,二人進入埃策爾王國後將獲得榮耀。但隨後另一位美人魚希格琳德(Sigelinde,此名被瓦格納借用至其他作品中)指出其姑母的謊言,並警告他們若前往埃策爾的領地,必將死在那裏[e][6][7]。此場景的地理位置存在多種可能性。根據《Þiðrekssaga》(《迪德里克薩迦》),事件發生在一個虛構的多瑙河與萊茵河交匯處[8]。後續提及的「Möringen」——即注定滅亡的戰士們渡河的地點——可能指代多瑙河畔的默林根,但也有學者認為更東部的大梅靈更符合文本描述[9]。

這段與《尼伯龍根的指環》劇情本身無關的故事,在瓦格納的創作中既呼應了《萊茵的黃金》開場場景,也體現在《諸神的黃昏》第三幕第一場的敍事中[4]。瓦格納最早將這一情節改編至其早期劇本《齊格弗里德之死》(後發展為《諸神的黃昏》),引入了三位無名「水少女」(Wasserjungfrauen)[f],並將其活動場景設定於萊茵河。她們在此警告齊格弗里德即將面臨死亡[4]。此後,這些「水少女」演變為「萊茵少女」(Rheintöchter),並被賦予獨立名字:弗洛希爾德(Flosshilde)、韋爾貢德(Wellgunde)與布隆琳德(Bronnlinde)[10]。當瓦格納以倒敍方式從齊格弗里德之死回溯至戲劇源頭時,最終確定了全劇的初始行動——阿爾伯里希[g]竊取萊茵黃金。他認為若黃金僅以無人守護的狀態被輕易奪取將缺乏戲劇張力,因此賦予萊茵少女「黃金守護者」的身份,並設定了「放棄愛情」的詛咒條件[11]。布隆琳德隨後更名為沃格琳德,可能是為避免與布倫希爾德產生混淆[10]。
瓦格納的創作可能還受到德國萊茵河傳說《羅蕾萊》的影響——傳說中一位因失戀投河自盡的少女化為塞壬,用歌聲引誘漁夫觸礁[12]。此外,希臘神話與古希臘文學亦是潛在靈感來源:赫斯珀里得斯神話中的少女守護者與《萊茵的黃金》中的萊茵少女存在相似性,兩者皆為三位女性守護一件被覬覦的黃金珍寶且均在敍事中遭竊[13]。瓦格納熱衷於閱讀埃斯庫羅斯的作品,包括其《被縛的普羅米修斯》,劇中由俄刻阿尼得斯或水仙女組成的歌隊與萊茵少女的塑造存在關聯——學者魯道夫·薩博(Rudolph Sabor)指出,俄刻阿尼得斯對普羅米修斯的態度類似於萊茵少女最初對阿爾伯里希的容忍[14]。希臘神話中的俄刻阿尼得斯是泰坦海神俄刻阿諾斯之女,而北歐神話(尤其是《詩體埃達》)中的巨人族海神埃吉爾同樣有九位女兒,其中一位名字意為「波浪」(德語「Welle」),這可能是萊茵少女之一「韋爾貢德」(Wellgunde)名字的詞源[14]。
瓦格納的歌劇並未揭示萊茵少女的起源,也未說明她們是否與其他角色存在關聯。儘管《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中大部分角色通過血緣、婚姻或雙重紐帶相互聯繫[h],幾位萊茵少女們卻顯得獨立無依。文本中未提及那位委託她們守護黃金的「父親」的身份[15]。部分瓦格納學者推測,這位父親可能是沃坦和眾神之父——甚至是一切造物的「至高存在」[16]。另一些學者則按德語「萊茵女兒」(Rheintöchter)的字面意義,認為她們是萊茵河本身的女兒[17]。
Remove ads
角色本質和屬性

萊茵少女被描述為戲劇中「最具誘惑力卻最難以捉摸的角色」[16],有分析認為她們象徵着「嬰兒式幻想的誘惑」[18]。她們本質上以統一體形式行動,個性複合而難以捉摸。除弗洛希爾德通過偶爾輕微的責備顯示出的隱含資歷——這一點在音樂上通過將角色分配給聲音較深的女低音或次女高音加以體現——她們的性格並無明顯差異[16]。蕭伯納在1886年對《尼伯龍根的指環》作為政治寓言的分析著作《完美的瓦格納信徒》中,稱萊茵少女是「無思慮、原始、半虛幻的存在,極似現代年輕女子」[19]。她們最初所展現的特質是魅力、頑皮與自然的天真,儘管知曉其潛在力量,她們也僅出於美麗而喜愛所守護的黃金[20]。但這種孩童般單純的表象具有誤導性——她們不僅是失職的守護者,在與阿爾伯里希互動時更顯露出挑釁、譏諷與殘忍[21]。當半神洛基告知萊茵少女,她們需要沃坦的幫助才能奪回黃金時,婚姻女神弗麗嘉稱她們為「水性楊花」(Wassergezücht),並抱怨她們以「詭詐的沐浴」誘惑眾多男性[22]。她們以魅惑的一面與齊格弗里德調情[23],卻在向布倫希爾德暗示的忠告時顯露出智慧的一面[24]。薩博認為萊茵少女們的個性融合了希臘俄刻阿尼得斯的「善良本性」與北歐埃吉爾之女的「冷峻特質」(包括溺殺人類的意願)[14]。
在《尼伯龍根的指環》系列中,沃格琳德(Woglinde)初登場演唱的歌詞以無實義音節為主:「Weia! Waga! ... Wagala weia! Wallala weiala weia!」這一創作在1869年《萊茵的黃金》及1876年全劇首演時引發爭議,甚至被嘲諷為「維加拉維婭式音樂」(Wigalaweia-Musik)[17]。瓦格納在1872年6月12日致尼采的信中解釋,「Weiawaga」源自古德語,與「聖水」(Weihwasser)一詞相關,其餘音節則有意模仿德語搖籃曲中常見的擬聲詞(如「Eia Poppeia」「Heija Poppeia」等)。因此,沃格琳德的吟唱既暗示萊茵少女的孩童般天真,又象徵自然的聖潔本質[17]。
萊茵少女們對黃金失竊的悲傷是深沉而真摯的。在《萊茵的黃金》結尾,當眾神通過彩虹橋進入瓦爾哈拉時,火神洛基刺地建議她們在沒有黃金的情況下,應該「沐浴於眾神新獲的光輝中」[25]。少女們的悲歌隨即化作嚴厲譴責:「唯有深處溫柔而真實」,她們唱道,「天上歡慶的一切皆虛偽而怯懦」[25]。至《諸神的黃昏》終幕,當她們奪回指環後,冷酷地將不幸的哈根拖入萊茵河底,展現出決絕的一面[26]。
在戲劇終了時,萊茵少女們是唯一明確存活的重要角色,除了少數幾個角色的命運尚不明了,絕大多數角色確已消亡[27]。儘管在這部四幕歌劇中的戲份相對簡短,但萊茵少女們卻是關鍵人物:她們對黃金的守護不周及對阿爾伯里希的挑釁,成為後續一切事件的肇因。瓦格納本人親自設計的「放棄愛情」條件使黃金得以被竊並鑄成一枚可統治世界的指環。由於戒指是由被偷的黃金製成的,只有將其歸還給萊茵少女在萊茵河水中的看護,才能解除其上的詛咒。因此,被盜物的歸還在瓦格納龐雜敍事中構建了統一主題的連貫性——即唯有物歸原主方能終結權力與貪慾的惡性循環[3]。
Remove ads
在歌劇中的角色

隨着音樂前奏達到高潮,沃格琳德與韋爾貢德在萊茵河深處嬉戲[28]。弗洛希爾德在溫和提醒她們作為黃金守護者的責任後加入她們[29]。尼伯龍根侏儒阿爾伯里希觀察着她們,並向她們喊道:「你們不妨向我靠近。」[30]謹慎的弗洛希爾德喊道:「保護好黃金,父親警告過我們要提防這類敵人。」[15]當阿爾伯里希開始粗魯地求愛時,少女們放鬆下來:「敵人陷入情網,這令我又驚又喜」弗洛希爾德說道,隨即展開了一場殘酷的戲弄遊戲[15]。首先,沃格琳德假裝回應矮人的示好,但在他試圖擁抱她時游開[31]。接着威爾岡德接手,阿爾伯里希的希望上升,直到她尖銳地回擊:「你這多毛又駝背的丑小子!」[32]弗洛希爾德假裝責備姐妹們的殘忍,並假裝自己展開求愛,阿爾伯里希完全被迷惑,直到她突然掙脫,與其他人一起唱起嘲笑的歌曲。被欲望折磨的阿爾伯里希憤怒地在岩石上追逐少女們,她們躲避他時他滑倒摔跤,最終在無能的憤怒中癱倒[33]。此時氣氛改變:一道突然的光亮穿透深處,神奇的金光首次揭示了岩石上的萊茵黃金。少女們唱起對黃金的狂熱問候,這激起了阿爾伯里希的好奇[34]。回應他的問題,沃格琳德和韋爾貢德透露了黃金的秘密:能從中鍛造戒指的人將擁有無盡的力量[35]。弗洛希爾德責罵她們泄露這個秘密,但她的擔憂被駁回——只有放棄愛情的人才能獲得黃金,而阿爾伯里希顯然深陷愛欲,不構成威脅[36]。但她們的自信是錯誤的;在羞辱中,阿爾伯里希決定統治世界比愛情更可取[37]。當少女們繼續嘲笑他的舉動時,他爬上岩石,發出對愛的詛咒,奪走黃金並消失,留下萊茵少女們潛入水中哀嘆她們的損失[38]。
Remove ads
當沃坦(Wotan)、弗麗卡(Fricka)與眾神開始跨越通往瓦爾哈拉的彩虹橋時,他們聽見萊茵河深處傳來哀傷的歌聲——少女們正為失去黃金而悲泣。沃坦既尷尬又惱怒,命令洛基(Loge)讓她們噤聲。然而,當眾神繼續前行時,此刻哀歌再度升起,夾雜着對眾神冷酷無情的尖銳控訴。[39][40]

時光流轉(至少跨越兩代人),在萊茵河蜿蜒流經的幽深林谷中,容顏不老的萊茵少女仍在為黃金悲泣,向「太陽女」祈求派遣一位英雄將黃金歸還[41]。齊格弗里德的號角聲傳來,他因狩獵迷路而來[42]。萊茵少女們以舊日的頑媚之態迎接,提出以他指間的戒指為代價提供幫助[43]。調笑間,齊格弗里德看似誠摯地允諾交出戒指[44]。但天真未褪的少女們卻陡然斂去嬉鬧,肅穆警告:若他不交出戒指則當日必遭橫死[45]。但無畏的齊格弗里德斷然拒絕威脅:「你們卻威脅我的生命與軀體,如果它的價值抵不上一根手指,你們便不會向我將它索取!」[46]少女們嘲笑他的愚蠢:「齊格弗里德,祝你好運!一位高傲的女子,今天會得到那東西,她會將我們的話聽取。」[47]齊格弗里德並未察覺她們指的是布倫希爾德。萊茵少女們游入深水,留下困惑的英雄獨自咀嚼話語,暗自承認方才險些沉溺於三人的魅惑之中[48]。
Remove ads
布倫希爾德在最後的獨白中向萊茵少女致謝,感念其「誠實的建議」[49]。萊茵少女們顯然已向她完整揭露了齊格弗里德受蠱惑與背叛的真相,並告知唯有將指環歸還萊茵河水方能破除詛咒[49]。布倫希爾德唱道:「我會給你們所要的東西,讓你們將我的骨灰拿去!火焰會將我吞噬,並滌除指環上的咒語!」[49]。她告誡萊茵少女未來需「悉心守護」,隨即縱身躍入齊格弗里德的火葬堆[50]。火焰沖天而起吞噬整個舞台,象徵諸神的覆滅[51]。隨着萊茵河水漫溢,萊茵少女現身直指指環[52]。覬覦指環的哈根高喊「指環被收了回去!」(Zurück vom Ring!)[52]——此為全劇最後一句台詞。沃格琳德與韋爾貢德擒住哈根將其拖入河底,弗洛希爾德則將奪回的指環高舉手中,與姐妹們在漸退的河水中盤旋游弋[53]。
萊茵少女的音樂
萊茵少女相關的音樂被瓦格納研究者詹姆斯·霍爾曼(James Holman)形容為「《尼伯龍根的指環》中具有開創性意義的音樂」[54];其他評論則強調其相較於全劇其他部分的獨特魅力與舒緩特質[54]。
在沃格琳德向萊茵河吟唱的開場曲《Weia! Waga! Woge, du Welle,...》(《萊茵的黃金》第一幕)中,旋律採用五聲音階,音符為降E、F、降A、降B與C[55]。歌曲以兩個音符的下行級進(F接降E)起始,這一音型貫穿《尼伯龍根的指環》全劇的眾多音樂動機[54]。該旋律本身在《萊茵的黃金》第二幕弗麗嘉斥責萊茵少女時重現,並在《諸神的黃昏》終幕時達到戲劇高潮——布倫希爾德投身火海後,萊茵少女從河中升起,自齊格弗里德的火葬堆取回指環[52]。其前五個音符經節奏變化後,成為《女武神》第三幕中沉睡的布倫希爾德的主題動機[56]。旋律的變體在《齊格弗里德》第二幕中轉化為森林鳥(Woodbird)的問候聲「嘿!齊格弗里德」(Hei! Siegfried)。根據德里克·庫克的分析,萊茵少女與森林鳥通過自然屬性相連[57],是「自然世界本質純真的盟友」[58]。
萊茵少女對黃金的喜悅與致意(《萊茵的黃金》第一幕中的「Heiajaheia, Heiajaheia! Wallalallalala leiajahei! Rheingold! Rheingold!...」)是一首凱旋般的頌歌,其旋律基於兩大音樂元素,這些元素在《尼伯龍根的指環》後續劇情中被不斷變奏並賦予多重用途。例如在《萊茵的黃金》第二幕中,當洛基(Loge)向眾神稟報黃金失竊及尼伯龍根的勢力隨之崛起時,原本歡愉的「Heiajaheia」呼喊轉化為陰暗的小調版本,音樂氛圍隨之扭轉[59]。而「Rheingold!」的重複吟唱沿用了沃格琳德開場曲中標誌性的下行級進音型(F接降E),這一音型在後續劇情中反覆出現:《萊茵的黃金》第三幕以該音型的小調變體象徵阿爾伯里希用黃金鑄造的邪惡指環[60];至《諸神的黃昏》中,它進一步演化為「對指環的奴役」主題——被貪慾支配的哈根以同樣的小調雙音音型向僕從發出「Hoi-ho」號令[61]。
哀歌《Rheingold! Rheingold! Reines Gold!...》(《萊茵的黃金》第四幕)由萊茵少女在《萊茵的黃金》結尾處吟唱,此時眾神正跨越彩虹橋進入瓦爾哈拉。它起始於致意曲的旋律,隨後發展為歐內斯特·紐曼(Ernest Newman)所描述的「縈繞心頭的失落之歌」,在逐漸增強的淒切情緒中被管弦樂隊的極強音淹沒,終結全劇[62]。《齊格弗里德》第二幕中,當齊格弗里德進入法夫納洞穴奪取黃金時,圓號奏響了該哀歌的慢速版本——庫克指出,這哀歌提醒着聽眾黃金的真正歸屬[63]。在《諸神的黃昏》序曲中,該哀歌作為管弦樂間奏《齊格弗里德的萊茵之旅》的一部分被激昂演奏,隨後隨着音樂轉入小調的「奴役」動機,陰鬱氛圍籠罩旋律[64]。
紐曼將萊茵少女與齊格弗里德的場景(《諸神的黃昏》第三幕第一場的「Frau Sonne...」和「Weilalala leia...」 )描述為「優雅的林間田園詩」[65]。該場景中與萊茵少女相關的音樂元素此前未曾出現;霍爾曼指出,這些音樂既暗示少女的誘惑本性,又傳達出一種懷舊與疏離感,隨着劇情接近尾聲[54]。
據記載,瓦格納於1883年在威尼斯去世前夜,就曾在鋼琴上彈奏過萊茵少女的哀歌旋律[66]。
Remove ads
舞台表現

自1876年《尼伯龍根的指環》全劇於拜羅伊特節日劇院首演以來,萊茵少女便被確立以常規人類形態呈現,而非美人魚或具備其他超自然特徵——儘管阿爾伯里希曾辱罵韋爾貢德為「冷漠的人兒,帶刺兒的魚!」(Kalter, grätiger Fisch!)[32]。由於其場景的舞台指示包含大量游泳、潛水及其他水中特技,如何呈現始終是對創意與想像力的考驗[67][23]。傳統上多依賴背景幕布與燈光營造必要的水域效果。二戰前,在科西瑪·瓦格納及她與瓦格納的兒子齊格弗里德的影響下,拜羅伊特對《尼伯龍根的指環》製作採取「壓抑的保守主義」政策[68]。儘管其他地區的演出已有創新,但直到195年戰後音樂節恢復後,拜羅伊特的《尼伯龍根的指環》呈現才出現顯著變化。尤其自1976年起,音樂節及其他地區的製作革新變得極具實質性與想像力[68]。
在1876年的原始製作中,萊茵少女通過半透明屏幕後的支架裝置移動。舞台機械與燈光效果由當時頂尖的舞台技術師卡爾·勃蘭特(Carl Brandt)設計[69]。科西瑪最終批准的一項革新是用巨大的隱形「釣竿」取代支架,將萊茵少女懸吊其上[70]。鋼絲技術繼續應用於齊格弗里德·瓦格納及其遺孀溫妮弗蕾德·瓦格納主理的拜羅伊特製作中,後者執掌音樂節至二戰結束。現代製作也採用類似技術:在1996年芝加哥抒情歌劇院《尼伯龍根的指環》製作(2004-05年重演)中,萊茵少女被懸掛於舞台上方的吊杆空間固定的蹦極繩上,實現了瓦格納預期的上下俯衝動作。舞台上的萊茵少女由體操運動員扮演並做對口型,而實際演唱由站在舞台一角的歌手完成[71][72]。

1951年拜羅伊特音樂節的製作由齊格弗里德與溫妮弗蕾德之子維蘭德執導,他打破傳統採用極簡主義舞台風格,以精妙的燈光效果取代傳統布景與道具。萊茵少女與所有其他角色一樣,身着樸素的簡單長袍,演唱時摒棄誇張表演,由此音樂與歌詞成為關注的核心[68]。維蘭德深受阿道夫·阿皮亞影響,後者所著《尼伯龍根的指環筆記》(Notes sur l'Anneau du Nibelungen,1924–25年)曾遭科西瑪否定:「阿皮亞似乎不知道1876年《尼伯龍根的指環》已在此上演,其舞台呈現是確定且神聖不可更改的」[70]。維蘭德與弟弟沃爾夫岡盛讚阿皮亞:「受音樂啟發而構建的風格化舞台與三維空間實踐——這些理念成為歌劇製作革新的初始動力,併合理催生出『新拜羅伊特』風格」[i][73]
在具有開創性的百年紀念版拜羅伊特《尼伯龍根的指環》(1976年,導演巴提斯·謝侯)中,萊茵少女的水下場景概念被完全摒棄,轉而將其置於一座大型水電站大壩的背風處,作為19世紀工業革命時期歌劇布景的一部分[74]。對於《諸神的黃昏》中萊茵少女與齊格弗里德的互動場景,謝侯顛覆了她們「永恆青春」的傳統設定,將其刻畫為「不再是歡快嬉戲的少女;她們變得疲憊、灰暗、憂心忡忡且笨拙」[75]。這一製作開創了「無限制的詮釋自由成為常態」的先例[68]。例如,尼古勞斯·萊恩霍夫(Nikolaus Lehnhoff)在1987年巴伐利亞國立歌劇院的製作中,將萊茵少女置於一間沙龍內,並讓火神洛基用留聲機播放她們在《萊茵的黃金》結尾的哀歌[76]。

彼得·霍爾在謝侯之後執導了拜羅伊特《尼伯龍根的指環》。其版本於1983至1986年上演,以最簡方式描繪萊茵少女的自然純真:她們赤身裸體[77]。基思·華納在其為科文特花園英國皇家歌劇院製作的《尼伯龍根的指環》(首演於2004至2006年)中沿用了這一特點。科文特花園發言人解釋稱:「少女是純真的孩子,自然的化身——一旦有人出現,她們便匆忙披上衣物以保護矜持」[78]。華納通過燈光營造水下效果,而霍爾則採用佩珀爾幻象:以45度角的鏡子使萊茵少女看似垂直游動,實際演員是在淺水池中水平着游泳[79]。
儘管萊茵少女的戲份在劇中相對較少,但這一角色常由因飾演瓦格納及其他劇目中主要角色而聞名的傑出歌唱家擔任。首位完整演繹萊茵少女三姐妹中的沃格琳德的是1876年拜羅伊特劇院的莉莉·萊曼[80]。1951年拜羅伊特音樂節在二戰後重啟時,這一角色由伊利沙伯·施瓦茨科普夫飾演[81]。其他拜羅伊特劇院的萊茵少女飾演者還有1965至1967年間聲演韋爾貢德的赫爾加·德內施[82]。洛特·萊曼於1912至1914年在漢堡國立歌劇院、1916年在維也納國立歌劇院飾演韋爾貢德[83]。其他錄製過萊茵少女的歌唱家包括為富特文格勒和RAI演繹的塞娜·尤里納克[84]、為喬治·索爾蒂版本演唱的盧西亞·波普與格溫妮絲·瓊斯[85],以及為卡拉揚版本演唱的海倫·多納特與埃達·莫澤[86]。
Remove ads
參見
- 埃吉爾與蘭的九個女兒——北歐神話中的海女以及人格化的海之女兒
腳註
參考文獻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