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希臘語言問題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希臘語言問題(希臘語:γλωσσικό ζήτημα,直譯:「語言問題」)指的是關於希臘民族應當以現代希臘的民間口語(通俗希臘語)還是以古典化的雅言書面語(純正希臘語)作為官方語言的爭論。這場爭論在19世紀和20世紀持續進行,並於1976年以民間口語勝出而告終,自此,通俗希臘語成為希臘的官方語言。

歷史
希臘的雙層語言現象自古就存在。[1][2][3][4]古希臘的文獻中處處體現着這種語言的二重性。前蘇格拉底時期的作者,如斐瑞居德斯、巴門尼德和色諾芬尼,更傾向於使用詩歌語言,而不是散文(即直述的寫作方式),因為詩歌語言被認為更古雅、更莊重。類似的例子也出現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最古老的東西自然就是最令尊敬的東西,人們指着來發誓的東西是最令人尊敬的」)。[5]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狄俄尼索斯·特拉克斯的《讀寫技巧》(這是第一部希臘語語法書,也是歐洲的第一部語法書),他在其中分析的是詩人們所用的更為古老的文學語言。正因如此,修昔底德選擇使用更為嚴謹的語言。例如,他在第三人稱代詞中用σφεῖς、σφῶν等,而不是當時通行的阿提卡方言形式αὐτοί、αὐτῶν、οὗτοι、τούτων或ἐκείνοι、ἐκείνων;又如一些早期的語音變化,他沿用的是舊形式:把雙寫的σσ寫作σρ,因為在他之前的年代,ρρ被念作ττ。此外,他還沿用一些逐漸消亡的詞形,例如從公元前5世紀起已逐漸由-οισι變為-οις的與格複數(如ἀνθρώποισι – ἀνθρώποις)。然而,那個時代的「通俗派」阿里斯托芬在《蛙》中卻仍寫道「τοῖς μὲν γὰρ παιδαρίοισίν ἐστι」(「對於孩子們來說是……」),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事實上,他甚至在《蛙》(第926行)里指責埃斯庫羅斯的戲劇語言過於晦澀,普通民眾難以理解。從中也能看出,當時的書面語和口語之間存在顯著差異。例如,詩人的語言常常混合一些古舊的成分(如悲劇中合唱隊使用的多利亞希臘語)。他們在創作中採用了多利亞、愛奧利亞、伊奧尼亞元素,形成了一種實際上不可能被任何人日常使用的「混合語」。
大約在公元1世紀,帶着某種浪漫情懷的阿提卡主義學者試圖進行語言改革——不是針對人們實際如何使用,而是規定人們應當如何使用,依據的是公元前5世紀的阿提卡方言。自此,著名的「語言問題」才正式開始,也就是當這種文體上的區分被當作規範推向廣大民眾之時。結果,書面語與民間口語之間的分化迅速擴大。
在亞歷山大大帝東征之後,馬其頓諸王的國家為了行政、貿易和外交需要,採用了阿提卡方言。阿提卡方言逐漸演變成希臘語的新形態——通用希臘語(它後來奠定了中古希臘語以及現代希臘語的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的變革,以及新宗教的興起,是通用希臘語確立和普及的主要原因。它在語音、詞法、句法和詞彙等方面都發生了變化。亞歷山大的語法學家發明了變音符號,並且認為通過使用阿提卡方言可以延續寫作的傳統,於是教授所謂「擬古主義」。這導致學者們轉向一種人為構造的書面語,同時也拉開了一場激烈鬥爭的序幕——極端古典主義者與極端通俗派的爭戰,而前者稱後者為「粗鄙之徒」。
在基督教教義的書面與口頭傳播中,最初使用的是通用希臘語。《舊約》被翻譯成這種語言,《新約》也幾乎完全以此寫成。但後來,三聖司教在正式的教會講道中採用了「阿提卡主義」,以便與希臘教育傳統相調和,並使信徒更容易接受。隨後,在東羅馬時期,書面語與口語之間的雙語(阿提卡語與通用語)現象促使二者各自分化。書面語言逐漸趨向句法上的繁複艱澀,而口語在語音和形態句法上不斷簡化,並先後吸收了大量外來詞:最初是拉丁語詞彙,後來又有斯拉夫語和土耳其語的成分。同時,由於外族的基督教化,新的借詞不斷進入。
Remove ads
當時的希臘語可以分為三個時期:早拜占庭時期(6—12世紀)、晚拜占庭時期(12—15世紀)和後拜占庭時期(15—19世紀)。[6]這些階段極為重要,因為幾乎所有「語言問題」的發展階段都能在其中找到。在第一個階段(尤其是12世紀,狄奧多羅斯·普羅德羅摩斯的所謂《乞丐普羅德羅摩斯詩》中),首次出現了使用通俗口語的文學作品;而在第二個階段,通俗語逐漸在書面語言中擴散(常與阿提卡語混合),並產生了後世大多數方言變體(例如騎士小說中所見的語言)。這種演變在1453年5月29日君士坦丁堡陷落於奧斯曼人之後加速進行。由於缺乏一個能夠作為紐帶的統一國家,遠離中心的居民之間缺少凝聚力,因此語言呈現出更大的分化。在缺乏國家與教育、又長期處於異族統治之下的環境裡,大量外來詞不斷湧入。克里特與塞浦路斯就是典型例子:它們在保留地方方言特點的同時,也大量吸收外來詞,並受到古老書面語的影響。在這之前的幾個世紀(10世紀下半葉),曾經有一股新的「阿提卡主義」浪潮,試圖阻止這種發展。當時許多文本(主要是宗教作品)被改寫成阿提卡化的風格;[7]而在安娜·科穆寧娜時代,[8]語言在句法層面上又經歷了一次「淨化」,出現了更精細卻已顯過時的句式。拜占庭時期的語言之爭主要有三大陣營:一是堅持使用聖歌及基督教禮拜語言(基於《福音書》的通用語)的人,二是阿提卡主義學者,三是支持口語派的群體(後兩個時期的主要代表)。
总结
视角
在奧斯曼統治時期,由於前拜占庭帝國領土的進一步乃至完全分裂、不同征服者對各地的統治以及各地區的隔絕,通俗口語最終定型為方言化的民間希臘語。在這一階段,它在詞彙上深受土耳其語和意大利語影響,不過隨着近代希臘國家的建立,這種影響逐漸減弱。當時一個顯著的趨勢是希臘人試圖在精神上與古代相連,他們常給子女和船隻取古代名字。[9]這種「崇古」是民族復興衝動的體現——民族覺醒後,渴望依託自身的古典遺產。值得一提的是,1638年出版的一部《新約》譯本因教會的強烈反對而被倉促撤回。這一事件成為後人避免重蹈的「反面教材」(直到1901年亞歷山德羅斯·帕利斯的譯本再度遭遇失敗為止)。
尼古拉奧斯·索菲亞諾斯是一位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大約在公元1540年出版了當時口語(他稱之為「通用語」)的第一本語法書。索菲亞諾斯的最終目的,是讓這種語言成為範本,使宗教文本能夠為不識字的人,乃至連婦女都能理解。[10]他的做法後來也被阿塔納修斯·蘭多斯(克里特的阿加皮奧斯,約1580—1657)效仿,用以面向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不久之後,在17世紀,弗朗西斯科斯·斯庫福斯與伊利亞斯·米尼亞蒂斯也選擇了這種風格(而非古典化的語言)。米尼亞蒂斯在其著作《修辭藝術》中甚至寫道:「……我們的通用語……在詞彙上十分貧乏……很多時候,我寧願保持沉默,哪怕有高遠的思想要表達,也不願用一種粗鄙的聲音,或完全希臘化的表達方式來說出來……」[11]然而,這些作者及其思想卻被著名的拉里薩學者亞歷山德羅斯·埃拉迪奧斯嚴厲斥責,認為他們可悲不堪,並對祖國有害。[12]
然而,隨着歐根尼奧斯·武爾加里斯的加入,語言之爭真正全面展開。他主張「通用語」(在此特指文盲大眾的語言)不適合用於具有更高威望的著作,並且對其加以強烈否定(這一點在當時因通用語的局限性,確實有其合理性)。對此,回應來自他當時已聲名顯赫的學生——伊奧西波斯·莫伊修達卡斯。他懷着對老師的敬意,在著作《地理學理論》中提出,應當使用一種更高雅的文體,但必須明確地與古典化的語言保持距離。可以說,他所倡導的這種語言(更確切地說是「文體」,此一術語正是由他引入)正是後來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純正希臘語」的先聲。他寫道:「我認為,傳教士在講道時,學者們在交談時,應當使用一種高於尋常的文體。歐洲人也同樣如此,這絲毫沒有損害到他們的普通民眾。」[13]他的文體特點,在這部作品中亦顯而易見。他為自己「樸素」的寫作方式辯解時寫道:
「我出於某些理由,決定用一種樸素的文體來編寫本書,但始終保留古人使用過的專門術語,並且時時將文體轉向更莊重一些,至少要更符合所討論主題的體面與得體。」[14]
由此,莫伊修達卡斯表達了他的信念——這一點與後來科萊斯的觀點十分相似——即語言必須經過「淨化」,不僅在語法上需要整理,而且要清除外來詞彙。需要指出的是,在那個時期,「通用語」這一術語(繼福音書的通用語與「文盲的通用語」之後)應當理解為「簡化的純正希臘語」,而絕不能與後來所說的「通俗語」(通俗希臘語)等同。
不久之後,季米特里奧斯·卡塔爾齊斯登上了舞台。他提出的「通用語」(此時這一不斷變化的詞,在這裡的含義是「人人使用的口頭與書面語言」)的範本,是君士坦丁堡的口語。這種口語雖充滿地方性成分,但卻是當時首都的日常語言。然而,這種「君士坦丁堡通用語」追隨者寥寥,只有少數人——如達尼埃爾·菲利皮迪斯與格里戈利奧斯·康斯坦達斯。他們效仿老師的做法,合著了《近代地理學》,卻讓卡塔爾齊斯忍不住喊出:「我的學生毀了我的語言!」[15]因此,很快連為數不多的支持者也拋棄了這種文體,轉而支持「簡化的純正希臘語」,後者最終也被普遍採用。就在這一階段,出現了尼基弗羅斯·塞奧托基斯——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神職人員。他在斯庫福斯與米尼亞蒂斯的基礎上更進一步,對純正希臘語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隨着時間推移,塞奧托基斯逐漸將純正希臘語中過度文言的成分清除,以至於後來受到康斯坦丁諾斯·薩薩的稱讚。因此,塞奧托基斯實際上站在「文言化的通俗語」與純正希臘語的交界處,被視為純正希臘語的主要奠基人。[16]
這一時期,還有兩位人物在「觀點」上(而非在實際影響上)頗為重要:約安尼斯·維拉拉斯與阿薩納西奧斯·赫里斯托普洛斯。他們二人同樣出自卡塔爾齊斯的學派。維拉拉斯和赫里斯托普洛斯都試圖把詩歌、歌曲中使用的語言推廣到語言的所有形式之中。維拉拉斯提出了極為激進、脫離歷史[17]且帶有強烈狂熱色彩的語音拼寫理論,結果自然適得其反;不過,他在某種意義上算是約安尼斯·普西哈里斯(後來的「語言鬥爭」代表人物)的先驅。1814年,他出版了一本名為《羅馬人的語言》的書,在書中主張徹底拋棄歷史拼寫。他寫道:「那些死氣沉沉的文言學究們從未研究自己民族鮮活的語言,從未觀察它最美麗、最恰當的表達,它的音變、縮略和其他自然特徵。若能運用這些來寫作詩文,就能使自然的語言得到裝飾與提升,正如其他所有語言的發展那樣。」[18]赫里斯托普洛斯則受愛奧利亞-多利亞理論影響,1805年在維也納撰寫了《愛奧利亞-多利亞語法,或當今希臘人所說的語言》(Αἰολοδωρικὴ Γραμματικὴ, ἤτοι τῆς ὁμιλουμένης τωρινῆς τῶν Ἑλλήνων γλώσσης)。在這本書裡,他直接將古代的愛奧利亞方言和多利亞方言與現代的「通用口語」聯繫起來。這一論點被許多著名學者所接受,包括科萊斯、卡塔爾齊斯、菲利皮迪斯、內魯洛斯、科德里卡斯等。然而,這並非源自他們知識的匱乏,而是由於當時的語言學尚未建立。最終,這一理論在喬治斯·哈齊達基斯的研究下徹底崩潰——他證明了當時(以及今日)的希臘通用語,實際上只是阿提卡希臘語經世紀演變的延續。相比之下,里加斯·費雷奧斯的貢獻要有限得多。他雖然最初也走學者路線,但逐漸卻轉向古風主義的陣營。
在那段時期,出現了一位語言問題歷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人物——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對科萊斯來說,語言是獲得教育的必要前提,而教育又是保障自由的根本。懷着這些理想,科萊斯認同啟蒙思想,並將其推廣到整個民族,不容任何例外。他的工作意義重大、備受尊敬,以至於在語言問題的爭論中,所有相關人士都認為他是對雙方陣營影響力最大的人物。
Remove ads
在近代歷史上,獨立後的希臘建立起一個由攝政政府主導、從德國移植而來的教育體系。這個體系是在德意志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條件下形成的,卻與這個因戰爭而滿目瘡痍的新希臘國家毫無相似之處。至於在文學、教育以及官方場合中該使用哪種語言,成為一個重大問題。通俗語被認為粗鄙、不夠規範,無法表達複雜的思想。

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作為希臘西化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在國家應以何種語言作為民族語言的爭論中,倡導對語言進行「淨化」,剔除外來成分,並提出並修訂了純正希臘語,它在1834年被確立為國家的官方語言。這種對通用口語的淨化,形成了為人所熟知的純正希臘語的樣貌。當然,它與埃曼努埃爾·塞奧托基斯和法那爾派的純正希臘語存在相當差異,因為後者正如前面所說,源於對書面語中過於學究化元素的「逆向淨化」。在科萊斯看來,這種折中的道路意味着:掌握現代希臘語至少需要具備古希臘語的基本知識。這一思想後來也為不少學者所支持,如阿希萊亞斯·察爾察諾斯。
對科萊斯最猛烈的攻擊來自法那爾人學者帕納約蒂斯·科德里卡斯。這位在學術上本應備受尊重的人,於1818年在其旅居的巴黎出版了《通用希臘方言研究》(Μελέτη τῆς Κοινῆς Ἑλληνικῆς Διαλέκτου),在書中主張新語言必須完全建立在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區的學者語言基礎之上,[19]而民眾的「粗俗語言」不可繼續在各種場合下使用。然而,儘管他的主張充滿矛盾,他所提出的語言風格與科萊斯的差異其實微乎其微,[20]卻在歷史上僅被記為科萊斯的敵人,其目的似乎僅僅是無的放矢地攻擊(正如季米特里奧斯·韋爾納扎基斯所指出的)。康斯坦丁諾斯·季馬拉斯也有類似看法,認為這種無謂的攻擊最終只傷害了他自己,因為他原本完全有資格在歷史上留下比一個「誹謗者」更高的地位。[21]布朗寧提供了一個典型的例子:[22]科萊斯把「ψάρι」(魚)更改為「ὀψάριον」,而科德里卡斯則改為「ἰχθύς」。顯然,科德里卡斯的攻擊讓不少學者和支持通俗語的人覺得可笑,因為他在九十八個方面與科萊斯一致,卻在僅僅兩個細節上竭力反對。事實上,從他們的寫作風格來看,兩人幾乎難以區分。
自然,雙方的攻訐不可能就此停止。因此,科萊斯的純正希臘語被法那爾派的雅科沃斯·內魯洛斯(後來倒戈站在科萊斯一邊)稱作「科萊斯體」,被內奧菲托斯·杜卡斯譏為「蹣跚文」(因為在兩種對立風格間搖擺不定)。而極端的通俗語派詩人狄奧尼修斯·索洛莫斯則極其不當,把科萊斯與最激進的古典主義者相提並論。[23]相反,幾年之後的季米特里斯·格利諾斯雖然在思想上與科萊斯有分歧,卻把他奉為偉大的人文主義者、通曉時代精神的人,並稱他為「在所有同時代和後來的學者中最耀眼的明星」。[24]不過,格利諾斯也指出,這並不意味着科萊斯所作的一切都正確,他之所以未能走得更遠,正是因為過於妥協。同樣的評價後來也出現在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著述中。科萊斯的根本目的,是反對走極端。比如,他特別批評了修昔底德的一個譯本,在該譯本中,(使用混合語言的)譯者擔心「ὀργίζομαι」(發怒)這個詞不被理解,就將其翻譯成了「χαλεπαίνω」(惱怒);同樣,他也批評通俗語派中過於激進的人,他們拒絕使用「σημαία」(旗幟)和「κήρυκας」(傳令官),卻用外來詞「παρντιέρα」和「κράχτης」。科萊斯在這一問題上的核心思想,正如比頓所總結的,可以歸納為三點:1.民族認同必須建立在對古希臘語的重新審視之上;2.新的書面語言必須與城市受過教育階層的現代口語語法相協調,作為民族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3.這兩點要結合在一個現實的規劃中,對口語中的弊病加以修正,使之更接近古典希臘語(例如,清除口語中廣泛存在的土耳其語及其他外來詞,如δεπαρταμένα代替意大利語dipartimento,ἀπελατζιόνε代替appellazione,並用新的詞彙代替土耳其語借詞κεχαγιάς、τζέργα等等)。[25]
除此之外,科萊斯還認為有必要從古希臘語中引入詞彙,以滿足語言的基本需要,這一點從前文已經可以看出。他還認為並明確指出,那些極端學者提出的「逐漸回歸古典語,以此作為民族自豪而非奴役的象徵」的主張,完全脫離現實。他甚至反對用古典語寫書:「誰會那麼愚蠢,或者誰會有那麼多閒暇,竟放下荷馬、柏拉圖……去讀這位新近冒出來的希臘化作者呢?」[26]而他試圖在各個層次和階層中,把語言與民族實際地結合在一起的努力,也確實引起了一部分學者和通俗語派人士的共鳴。
科萊斯提倡的書面語的一個樣例如下:
«Ἡ μήτηρ μου ἔλαβεν ἐλευθερωτέραν ἀνατροφήν, διότι εὐτύχησε νὰ ἔχῃ πατέρα Ἀδαμάντινον τὸν Ῥύσιον, τὸν σοφώτατον ἐκείνου τοῦ καιροῦ εἰς τὴν ἑλληνικὴν φιλολογίαν ἄνδρα, ὅστις ἀπέθανεν ἓν ἔτος (1747) πρὸ τῆς γεννήσεώς μου. Αὐτὸς ἐχρημάτισε ἔτι νέος ὤν, διδάσκαλος τῆς ἑλληνικῆς φιλολογίας εἰς Χίον· Μετὰ ταῦτα ἦλθεν εἰς Σμύρνην, ὅπου ἐνυμφεύθη χήραν τινὰ Ἀγκυριανήν...»[27] |
可以看出,他在一些按語法本應使用與格的地方避免了這種用法,只是簡單地將個別詞彙替換成更文雅的詞,而並未改變句法結構,卻仍然意在向古典語靠攏。正如他所主張的那樣:「如果一本書寫得仔細,並且……用一種適度修飾過的語言來寫,那麼(即使是文盲)也會逐漸學會修飾他們的口語。」[28]
他在兩派中都有朋友,但這並不意味着沒有敵人。事實上,他確實同時遭到了雙方的攻擊,不過原因完全不同。通俗語派的人指責他試圖塑造一種語言形式,這種形式既不像當時的通俗語那樣自然演變而來,也不像學者們的純正希臘語那樣有傳統承續。
他與帕納約蒂斯·蘇措斯之間自然也爆發了爭論。按照當時的慣例,蘇措斯出版了一本書,不僅指出,而且嚴厲批評了其他作者的語病。他的立場是:語言使用中的錯誤可以通過與古希臘語更緊密的聯繫來解決。在他看來,大部分錯誤源於古典語與科萊斯式的純正希臘語之間不當的混合,他稱這種混合為「不充分的折衷」。這種情況延續下去:有些人依照古典語來校正科萊斯的著作,另一些人則依照通俗語來改動。前者批評科萊斯,並不是因為他知識匱乏(正如喬治斯·哈齊達基斯所指出的,這種情況極為少見),而是因為他走在一條「中間道路」上,既與最不識字的人保持距離,也與民族中最有學問的學者拉開差距。這條中間道路建立在這樣一個問題上:「難道只有博學之人必須向無知者的語言靠攏,而不是讓無知者提升到博學者的語言嗎?」最後總結為一句話:「既不做庸俗者的暴君,也不做他們庸俗性的奴隸。」

與雅各布·菲利普·法爾默賴厄的反希臘觀點(見下文的哈齊達基斯-克倫巴赫爾之爭)相對,出現了一場極端古典主義運動的大規模復興,其主要支持者包括內奧菲托斯·杜卡斯、斯特凡諾斯·科米塔斯、康斯坦丁諾斯·伊科諾莫斯(他原先是科萊斯的支持者)、斯卡爾拉托斯·維贊蒂奧斯、克萊翁·里佐斯·蘭加維斯、帕納約蒂斯·蘇措斯、阿納斯塔西奧斯·喬治亞季斯·萊夫基亞斯、斯皮里宗·贊貝利奧斯、喬治斯·米斯特里奧蒂斯等人。這一團體的最終目標是讓希臘語逐步回歸到阿提卡方言,即公元前4世紀最典範的古希臘語形態。斯卡爾拉托斯甚至設想,也許在五十到一百年之內,人們就能完成這一不可能的事業。[29]為了實現這個確實幾乎不可能的目標,他主張將阿提卡方言的語法作為標準,並加以簡化(至少在最初幾年),甚至推行到小學教育中去。他自1854年至1878年(即其去世之年)擔任初等教育總監。這一運動的觀點極端而又帶有浪漫的烏托邦色彩,因此除了上述學者之外,幾乎無人追隨。該思想的主要領袖是帕納約蒂斯·蘇措斯,他於1853年出版了《書面語新學派,或人人皆可理解的古希臘語復興》(Νέα σχολὴ τοῦ γραφομένου λόγου ἢ Ἀνάστασις τῆς ἀρχαίας Ἑλληνικῆς Γλώσσης ἐννοουμένης ὑπὸ πάντων)一書,在其中,他摒棄了當時(科萊斯所用)的語言形式,轉而以古典或接近古典的形式取代(如ἦν/ἤμην)。不過,蘇措斯與其他人的最大區別——雖然僅此一條,卻極為關鍵——在於:蘇措斯追求的是徹底以「阿提卡語體」取代一切文體,而其他人則有意將這種阿提卡化的文體限制在教育和官方書面語的範圍之內。
各方的反應似乎都迅速而激烈。關於這一話題的重要研究包括由康斯坦丁諾斯·阿索皮奧斯匿名出版的《蘇措斯文獻》(1853)、康斯坦丁諾斯·孔托斯所著的《語言學觀察》(1882),以及季米特里奧斯·韋爾納扎基斯編寫的《偽阿提卡化批判》(1884)。第一部作品只是對蘇措斯的言辭進行了審視(並與其立場一致),第二部則指出了所有「語言淨化者」的文學錯誤,從科萊斯到蘇措斯(儘管沒有做出更深的分析,且包含一些毫無根據的指控[30]),而第三部則試圖批評孔托斯為偽阿提卡化,但未能成功。
在大約相同的時期,其他通俗語派支持者認為,語言問題本身始於1821年的革命,而如前所述,雙語現象自普魯塔克和琉善的阿提卡化時期便已存在。[31]科萊斯甚至被布魯格曼陣營用粗俗的方式指責,認為他「搞砸了一切」,因為他選擇停止走向通俗語的道路:「可憐的他,本該將古希臘元素與通俗語結合,卻反而把通俗語的元素與古希臘語倒過來結合。然後,他還設立了……詞彙的迫害,卻沒有考慮到他後來的追隨者會走得更遠,刪掉每一個非古典的詞彙,而這對於語言來說,是失去了根基……」。[32]基於這一邏輯,通俗語派認為,隨着新成立的希臘國家進入歐洲,語言應當得到補充和豐富,但不應清除其中大量的土耳其語和威尼托語元素。因此,他們指責科萊斯用古典詞彙替代了已經在希臘語中混雜了幾十年的土耳其和意大利詞彙。他們認為,必須勇敢地根除純正希臘語,因為它扼殺了寶貴的民間詩歌和歌曲。他們的證據是一些歌德的德語翻譯。根據布魯格曼的觀點,通俗語應該基於維拉拉斯的觀點,最終目標是「這種共同的語言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靈活運用,但它的規範性總是保持不變,以便希臘和土耳其的各地都能毫無困難地交流。」[33]這樣,虛偽的教育(即學校中的書面語言教學)將逐漸衰退,學生們將獲得真正的知識。他們的論據之一是喬治斯·米斯特里奧蒂斯的演講在「女學生」中接受的情況,這與官方國家的默許有關。純正希臘語被描述為「疥瘡」,因為它使希臘人停止了任何文學創作。最具代表性的表達之一便是:「純正希臘語的害處遠遠大於它的好處,那些空洞的頭腦數不勝數」(《現代語法學》25頁)。如今,大多數著名的語言學家和文學學者的觀點已經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像喬治斯·巴比尼奧蒂斯就認為,關於語言問題的爭論是積極的,因為許多人致力於語言在雙重傳統中的更深層次的培養。[34]最終,布魯格曼對卡爾·克倫巴赫爾和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的觀點表示了認同,[35]承認「純粹的」普西哈里斯提出的方案不能代表真正的民眾語言,因為「他們誤解了它」。他進一步指出,應該有一個妥協,但這個妥協不應基於科萊斯,而應基於維拉拉斯的觀點。換句話說,語言不應僅僅向中庸之道靠攏,而應更多地向各地的「方言」適應。根據這一邏輯,純正希臘語應當「從其寶座上降下幾個台階」,並應追隨生動的通俗語,通俗語將保持原樣,僅添加極少的來自「詞彙寶庫……它在純正希臘語中被浪費和保存的詞彙」。在這一問題上,巴比尼奧蒂斯的觀點完全不同,他認為,基於古代語言的這一內部借用和淨化語言是健康的,目的是避免外來詞彙在當時的通俗語中泛濫。正是「啟蒙者」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正如巴比尼奧蒂斯繼續說,拯救了語言免於遭遇混合化,還有其他民族的教師也做出了貢獻。同樣,普希哈里斯關於語言的立場也被認為是極端的。[36]
19世紀幾乎所有歐洲民族共同的特點——對民族身份的追尋,推動了民俗學的興起與發展。結果,在隨後的幾年裡,民間音樂的收集和出版數量大大增加。狄奧尼修斯·索洛莫斯在伊奧尼亞學派所創造的傳統,由雅科沃斯·波利拉斯、亞歷山德羅斯·瓦拉奧里蒂斯等人延續,他們受歐洲相應文學運動的影響,主要關注歷史題材,但更多的是社會問題,其中可以找到民間主義運動的根基,因此也為隨之而來的語言問題的對立奠定了基礎。當然,值得一提的是,在長期受威尼斯和英國統治的伊奧尼亞群島,古典主義並未得到支持,而早在索洛莫斯之前,民間傳統在詩歌中就已得到了培養。[37]
因此,科萊斯再次招致了反對,他被通俗語支持者指責為對語言進行人為干預,而被古典化支持者認為他拒絕語言傳統。為了推廣某種語言形式所展開的鬥爭多且複雜,涉及到希臘民族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問題。無論如何,在文學領域,1888年約安尼斯·普西哈里斯的《我的旅行》一書出版,給後來的通俗語使用提供了推動力。普希哈里斯的語言正如許多人所指出的(包括他意外的盟友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他寫道:「如果我們按《旅行》中的語言寫作,就不會像我們講話那樣寫作」《赫斯蒂亞》第660期,第670頁),是一種規範化的通俗語,[38]但這種語言是他自己發明的,因此學者們稱之為「偽通俗語」。[39]普希哈里斯突然成為了中心人物,因為他開始遭到大多數人的攻擊,而少數人則將他視為語言上的神化人物。原因不僅是他輕鬆創造出一些不存在且陌生的詞彙(如「Χιό της Χιός」「δάσητα」「φώσια」「πνὲς」以及「ἀναπνές」等),還因為他用土耳其語借詞替換了那些華麗的學術詞彙。例如,他用「τυφλοσόκακο」代替了「ἀδιέξοδον」。接着,他不僅僅滿足於這些,他相信自己創造的通俗語是古典語言的生動後代,於是他開始對現有的語言結構進行實驗。換句話說,當古典主義者和學者將希臘語「古典化」時,普希哈里斯則「現代化」了古希臘語,引入了任意的語言形式,這些形式與他的死敵們的形式十分相似。這些借詞(甚至包括從純正希臘語中借來的)被他與自己的形態學規則結合起來。於是,關於他矯揉造作的指責也隨之而來,[40]因為事實證明,新興的通俗語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吸收了許多學術元素。比如「συθήκες」「σκετικός」「ἀρφάβητο」「πομονή」「έχταση」等詞彙。因此,他的書面語言包含了從未被任何人使用過的、作為真正通俗語的詞彙。這也成為了「濫造」和「粗俗」的開始,將矛盾推向了另一個極端。[41]事實上,喬治斯·德羅西尼斯承認,自從《赫斯蒂亞》開始轉載普希哈里斯語言風格的文章後,這家報紙的訂閱者大量流失,最終陷入了困境。[42]
Remove ads
总结
视角

古代傳承下來的雙層語言現象,其真實性得到了雙方學派所有希臘學者的支持,甚至連大多數通俗語派也不例外,只有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在其1833年發表的《幻象》一書中)和季米特里奧斯·韋爾納扎基斯持不同看法。教授喬治斯·哈齊達基斯批評羅伊德斯無視自己在《雅典娜》文藝期刊(第五卷,第181頁及以下)中所提供的證據,因為羅伊德斯主張,唯有在當代希臘才存在雙層語言現象,而在他看來,這是極為可憎的。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溫和的通俗語派代表狄奧尼修斯·索洛莫斯。他在《致最博學者的對話》一文中與一位「雜糅派」學者辯論時承認,雙層語言現象在古代同樣存在,並且承認柏拉圖的寫作並不等同於當時希臘人的日常口語。這部作品後來更成為通俗語派的「福音」。韋爾納扎基斯也承認,在那個時期要使用完全不含純正希臘語成分的民間口語是不可能的。他說:「治癒這種語言疾病的最佳辦法,本來當然是徹底割裂並解放民間口語,使之完全純粹、不受古希臘語影響,但這已不可能」,又在別處寫道:「今天單靠(民間口語)已不足以應付需要,這種貧乏我已詳盡論證並加以解釋。」[43]這位教授的觀點是:我們理應將民間口語與純正希臘語分開,但既然這不可能,就必須在民間口語中補充純正希臘語所具備而其自身所缺乏的詞形和句法,使其能為所有人所用——「因此我們必須使用一種二者的混合體」。
很自然地,他遭到了喬治斯·哈齊達基斯的抨擊。後者寫道,他一定是得了某種腦疾,才會主張應當先把語言分開,再重新拼合成一種混合體。[44][45]
值得注意的是,韋爾納扎基斯和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雖然都是民間口語的擁護者,卻因為當時未經錘鍊的民間口語存在許多缺陷,仍然選擇用嚴格的純正希臘語來寫作,甚至接近於「超純正希臘語」。當然,韋爾納扎基斯也承認:「這場鬥爭並不是關於原則和理念的,而是關乎人與人之間的攻訐。」[46][47]這一點從許多資料都能看出來。例如,德國的通俗語派學者卡爾·布魯格曼就指出,[48]希臘民族正被那套生鏽的書面語言吞噬——它是民族的疾病;就像意大利語(雖然著名語言學家喬治斯·巴比尼奧提斯[49]、德國學者海曼·施泰因塔爾[50]等人認為情況有所不同)必須將拉丁語丟進垃圾堆,意大利民族才能繁榮一樣,希臘民族也必須拋棄純正希臘語。否則,語言問題給希臘文化造成的巨大損害將繼續下去。他還說,正如中世紀的拉丁語曾阻礙了各民族自然語言的發展,純正希臘語同樣正在摧毀希臘民族。
這種激烈的人身攻擊在卡爾·布魯格曼的言論中體現得尤為明顯。他指責哈齊達基斯過於極端,因為後者竟敢與自己的老師卡爾·克倫巴赫爾相對立,而且在個人寫作中使用嚴格的純正希臘語,卻公開宣稱支持較為簡化的純正希臘語[51]——正如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所做的那樣。布魯格曼甚至罵他是「無恥的」哈齊達基斯,說他不過是個沒有影響力的教授,寫的不過是「幼稚、噁心、下流的詭辯」,並且試圖證明克倫巴赫爾是個仇視希臘的人。他甚至到了這樣一個地步:在對外的言論中把哈齊達基斯描繪成「國家威脅」,稱「這樣一個卑劣之人……就是民族的危險……還是個自封的危險人物」。[52]當然,這顯然是過於極端的解讀,因為哈齊達基斯本人在別處也寫過,大多數語文學者連替克倫巴赫爾解鞋帶的資格都不配有。[53]
支持「簡化純正希臘語」的人,並不像那些極端派——例如「雜糅派」(把嚴格的純正希臘語和純粹的阿提卡語混合,製造出「怪物」)、「阿提卡派」(主張經過兩三代的過渡,就立刻回歸柏拉圖、德摩斯梯尼黃金時代的語言,如帕納約蒂斯·蘇措斯所倡導的)、或「長發派」(以最不識字者的語言為範本,排斥一切其他形式)——那樣激進。他們主張的是:我們很幸運,擁有兩件衣裳,一件是日常的,另一件則是正式和節慶時的。[54]
純正希臘語擁護者的看法是,應當對這種語言加以簡化,尤其是在小學低年級的教學中,但同時要保留這兩種語體的並存。還有一些人,比如安德烈亞斯·斯基亞斯,則主張逐步引入那些在日常口語中原本無用的詞彙或形式,讓它們通過書面語慢慢進入並最終在日常口語中占據一席之地。同時,他也表示,無論是純正希臘語還是民間口語,都不適合在所有場合使用,而必須根據需要交替運用。[55]

語文學家兼語言學家喬治斯·哈齊達基斯主張在合理範圍內使用純正希臘語,這些界限不應被任何一方逾越。尤其是,他批評了一些當時極端的新阿提卡派著名學者,指責他們「違背自然」,試圖割斷新希臘語的自然延續(在他看來,這就是純正希臘語)。在他眼中,唯一的例外是康斯坦丁諾斯·孔托斯,因為後者曾教導說:「與其追求過於精緻的表達卻犯下嚴重的語病,不如滿足於大家常用的語言。」此外,他在《語言觀察(為修正我們的現代語言)》一書中所提出的一些詞彙,其實來源於中世紀或更晚時期,而非古希臘語。他深信,一大成就是:掌握這門新語言的人,憑藉它相當程度上的新語法和新句法,能夠相對容易地理解公元前5世紀的古典希臘語。他在《希臘語言簡史》(第十四章《論我們的新書面語》,1915年出版)中明確寫道:[56]
「……很明顯,我們既沒有使用阿提卡方言——如有人惡意誹謗所言那樣——也沒有使用任何古代或《福音書》的通用希臘語,因其保持不變,已然陳舊,對我們今天無用(因此,說『書面語就是《福音書》的語言』顯然不屬實)。同樣顯而易見的是,我們並沒有創造,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創造一種新的語言,而只是恰當地改造並儘可能調整我們從古至今所聽到的語言(即純正希臘語),以適應現代需要。所以,凡是宣稱我們民族被強加了一種新的、外國的、古老的、陌生的語言的說法,完全是不實的。」
哈齊達基斯的信念是:一個民族完全可以在不同場合(例如文學中)使用同一種語言的不同形式,但這並不意味着其中某一種必須成為國家的官方書面語(統一範本)。[57]和他的老師康斯坦丁諾斯·孔托斯一樣,他也被指責是有意為恢復色諾芬、伊索克拉底的「黃金時代的阿提卡方言」開路。然而,在許多著作中,他明確否認了這一指控,並提出多種理由說明這既不是他的目的,也不應當發生。他甚至以實際例子加以說明,比如不再使用不定式、單詞化的將來時、第二變位動詞、古代的發音方式等等。[58]他曾直言:「我早就聲明過,如果真的去追求並恢復古希臘語,那將是民族的災難……柏拉圖和色諾芬的語言完全不符合我們當下的需要和能力。」[59]他是普西哈里斯最大的敵人——二人還是同行。他抨擊普西哈里的語言虛假無用,並稱其本人是一個嚴重的民族威脅(參見第34頁、41–45頁)。同時,他譏諷這些激進的通俗語派,指出他們雖然人數不多,卻彼此爭吵,爭論誰寫的是「正確的」民間口語,誰寫的是「錯誤的」。最後,他與安德烈亞斯·斯基亞斯的觀點類似,認為人們擁有兩件衣裳:一件正式的,一件日常的。就像古代希臘人把詩歌語言與日常口語區分開來一樣,他相信民間口語不應被連根拔起,而應當加以修飾、精煉。他寫道:「我從未稱它為野蠻或腐敗的語言,恰恰相反,我盡力去培育它;如果我沒有弄錯的話,我為它所做的努力並不比今天那些讚美它的人少。」[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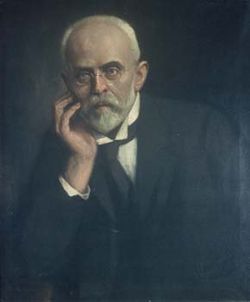
雅各布·法爾默賴厄的觀點在當時整個歐洲,尤其是在德國,得到了廣泛的接受。著名的拜占庭學者克倫巴赫爾(以及卡爾·布魯格曼)也被指責並非例外。[61]按照批評者的說法,法爾默賴厄那些所謂「科學的」論證(如今被視為反希臘、反科學[62]),在某種程度上深刻影響了克倫巴赫爾。後者眼見一個在他看來「種族混雜」的民族,卻想藉助自己的語言去接近古典希臘文明,於是採取了極為激進的立場,支持當時各種地方方言中最「純粹」的民間口語。正是針對這些觀點,著名而且在國際上享有盛譽的語言學家喬治斯·哈齊達基斯(康斯坦丁諾斯·孔托斯的學生)挺身而出加以反駁。
他指責克倫巴赫爾在相關問題上(即語言學和語言歷史延續性)學識不足,帶有明顯偏見,因而在論述中出現錯誤和矛盾。[63]哈齊達基斯首先強調的是拉丁語與古典希臘語之間的差異。克倫巴赫爾的主張是,按照其他民族拋棄拉丁語的例子,希臘也必須完全捨棄古代希臘語的成分(比如用「καμπίσιος」代替古希臘語中早已生僻的「ἀγροτικός」,或用「ἀπέθαντος」代替「ἀθάνατος」)。[64]對此,哈齊達基斯則從語言學角度解釋了通用希臘語的緩慢演變,並指出在各個時代,即便是不識字的普通人,也多少能夠理解一些雖古老卻仍在使用的詞彙和句式,例如拜占庭帝國時期。而拉丁語則從未以「活態」(即帶有一定自然變化)的形式存在於任何一個國家的日常生活中。換言之,使用拉丁語的人只能去模仿、抄寫、復活那些已經失傳、不再使用的孤立而過時的語法形式。他最後強調說:「即便是瞎子也能看出,對大多數人、對整個民族來說,當今書面語的句式遠比這新造的東西更加清晰、親切。而要拋棄我們現在使用的書面語,轉而採用中世紀時的拉丁文,這是完全錯誤的,從此以後也應當不再被允許。」[65]事實上,克倫巴赫爾甚至把阿提卡方言(逐漸演變為通用希臘語)的優勢地位,與拉丁語的情形作了類比。對此,回應顯而易見:在古代,所有希臘人雖然地域不同,但總還是能夠理解其他方言,只是在極端情況下才會有一定困難。然而在哈齊達基斯所處的時代,如果讓君士坦丁堡居民和克里特人、塞浦路斯人或塞薩洛尼基人僅憑各自的方言口語交流,那幾乎是不可能的,溝通困難到了極點。[66]
持相反意見的是狄奧尼修斯·索洛莫斯,他被稱作「當然是極有價值的詩人,但對希臘語言及其歷史卻完全陌生」。[67]單憑這一點,就讓當時通俗希臘語成為全體希臘人的「共同語言」變為不可能。相反,報刊、學校、教會、法庭、軍隊、國家等等所使用的純正希臘語對希臘人來說卻是熟悉的,[68][69]因為「今天城市和鄉鎮裡所說的語言,與波利比烏斯所用的通用希臘語相比差異更小,而那種通用希臘語與荷馬所用的語言差距反而更大」。[70]事實上,哈齊達基斯甚至還拿親屬(具體來說是他的外甥們)來做論據,說他們會請他用書面語中的對應詞來解釋一些外來詞或根本不常見的民間詞。[71]反過來,極端的通俗語派卻聲稱他們是在用自然語言寫作,但他們往往要先花很多小時琢磨每個形式和詞彙,這恰恰反映了當時通俗希臘語的狀態,也說明了與普西哈里斯一派相關的問題。[72]然而,純正希臘語卻能夠被非專業的語言工作者熟練使用(哈齊達基斯特意舉了記者的例子)。因此,即便在那個年代,文盲也能勉強接觸這種語言,而它的演變正是經由通用希臘語承繼自阿提卡希臘語的。[73]由此可見,那位德國拜占庭學者的看法——即書面語(即剛剛從通用希臘語中被命名出來的純正希臘語)是「由活的和死的詞彙拼湊而成的混合物」——完全是錯誤的。他所舉的例子如「οἶκος」(家)、「οἶνος」(酒)、「ὕδωρ」(水)。對此的回答同樣是:「……說古希臘語對現代希臘人和其他人一樣已經死去,這也是錯誤的。因為我們由於新語與古語之間極大的相似性和在許多方面的一致性,比所有其他人更容易學習、理解並體會它。這一點,我相信,任何理性的人都會承認。」[74]
此外,在其論著中,克倫巴赫爾把書面語與口語的分野追溯到前一個世紀,但他在別處卻因偏袒而受到指責——他曾讚揚一部雅科沃斯·波利拉斯的《伊利亞特》譯本,而那時這部譯本甚至還未付印。按照他的觀點,希臘缺乏「工程師、建築師、化學家……」的唯一原因在於純正希臘語,而不是巴爾幹地區劇烈的政治變動。[75]這也正是為什麼不僅要保留充滿方言色彩的通俗語裡的外來詞,而且還應該儘可能多地吸收它們,作為「混合」的見證。例如,醫學術語就不該用希臘語自造(如「Οφθαλμίατρος」(眼科醫生)、「Ωτορινολαρυγγολόγος」(耳鼻喉科醫生)等),而是應該直接照搬自其他語言——對此,哈齊達基斯批評這是荒謬的,簡直是「拿小麥換橡子」。[76]他指出,這種外來語的融入並不是源於民族「混合」,而是出自長期的奴役和暴政壓迫。在他看來,簡直不可思議:比如,一個希俄斯島人竟會用外來詞來代替伯羅奔尼撒地區已經存在並普遍使用的希臘詞,反之亦然。論證結束時,他總結道:「因此,必須要麼完全不借詞,要麼在借用時保持其形式不變,以便清晰易辨。」從歷史角度看,克倫巴赫爾對普西哈里斯及其追隨者的盲目崇拜也頗為重要。他甚至聲稱,就像有塞奧佐羅斯·科洛科特羅尼斯和康斯坦丁諾斯·卡納里斯的雕像一樣,也應該為普西哈里斯、羅伊德斯、科內梅諾斯和波利拉斯豎立相應的雕像。[77]

在19世紀80年代,來自巴黎的語言學家約安尼斯·普西哈里斯登上了舞台。1888年,他先是在法語中出版了一本題為《語言學與歷史問題》(Questions d’histoire et de linguistique)的語言學著作,同年又出版了所謂的「宣言」——《我的旅行》(Τὸ ταξίδι μου)。這本旅行記本質上是一部形式特殊的文學作品,其目的在於展示(在他理解下的)通俗語如何既能用作書寫語言,又能用作口語,成為全民共同的表達工具。然而,正如前文也提到的那樣,引人注目的是:普西哈里斯一方面寫的是母語、自然、不加修飾的通俗語,另一方面卻承認自己在書中「不經過幾個小時的反覆思考,我寫不出一個詞、一個音節」。
這位語言學家在整個語言問題的歷史中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因為他不僅在作品中提出了種種語言學觀點和現象的解釋,更主要的是,他是按照當時新興的語言學方法來行事的。受其導師索緒爾的影響,他把全部重心放在當時文盲所說的活的口語上,而不是書面語,也不是書面語的歷史演變。同時,普西哈里斯深受早期(1880年前)的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影響,堅持認為語言的典範應該是那些完全文盲的說法,而不是普通人,因為後者的詞彙里,隨着演變過程,已經固定下了許多書面語色彩的形式。基於這些觀點,普西哈里斯被認為是極端激進的通俗語派之父。他甚至主張,語言絕不應當像學者那樣通過不斷的小修小補來「淨化」,卻反而認為必須對口語進行各種全面的規制和規範(同樣是不合自然的)。正如喬治斯·巴比尼奧蒂斯所指出的,普西哈里斯極端而絕對,以至於把所有(已被廣泛接受的)書面語形式出現在口語裡都視為不可接受的妥協與背叛。他甚至毫不猶豫地指責像科斯蒂斯·帕拉馬斯和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這樣的通俗語派學者是叛徒和投降派。[78]他那種極端文風的一個例子是這樣的:「Οἱ ἄλλοι μας ἦχοι μορφωνόντανε ὣς τώρα εἴτε μὲ σφάληγμα -σωστότερα μ’ ἕνα πρωτοστούμπωμα… εἴτε μὲ πέρασμα, δηλαδὴ μὲ μόρφωση στενάδας στὸ γλωσσόσπιτο κάπου… ἐνῶ οἱ προηγούμενοι γίνουνται μ’ ἕνα κίνημα καὶ σώνει, αὐτὸς θέλει τὸ λιγώτερο δύο κινήματα.」(我們的其他音素至今的形成方式,要麼是通過阻塞——更準確地說是通過一種初始阻擋……要麼是通過通過,也就是說通過在口腔某處形成狹窄通道……而前面的那些音素是通過一個動作就完成的,這個音素則至少需要兩個動作。)[79]普西哈里斯最大的,也是最觸犯公眾情感的錯誤,在於他把語言視為一種未經過歷史積澱、未受書寫傳統影響,更與受過教育者的語言毫無關係的東西。這種觀點完全是脫離歷史的。[80]
對他最嚴厲的批評來自喬治斯·哈齊達基斯(見前文),後者用各種方式稱他為危險人物,把他看作一個對希臘情況一無所知、來自國外的破壞者。然而,儘管他對一切持不同意見的人表現得極端好鬥,他對語言問題最終的解決卻做出了至關重要的貢獻。他提供了一個語言模式,後來的語言學家(如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此基礎上加入了書面語中已經固定的形式,同時避開了他那些過於激烈的語言主張。這就標誌着從普西哈里斯的「舊通俗語派極端主義」向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新通俗語派溫和主義」的過渡,而後者對前者有着強烈的質疑。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1917年通俗希臘語進入學校時,是推動這一變革的核心人物。他當時作為新通俗語派的領袖,卻並未把語言問題與政治聯繫起來,因為他不是左翼,而只是一個自由派學者。1941年,他出版了《國家語法》(即《特里安塔菲利季斯語法》),用語言學的方法把通俗希臘語調整成幾乎就是今天所見的形式。
著名語文學家約安尼斯·斯塔馬塔科斯,作為純正希臘語的支持者,更偏向保守而非極端,因特里安塔菲利季斯支持通俗語的立場,多年來一直是他擔任語言學教席的阻礙。不同於前述那些常常演變為惡毒人身攻擊的論戰,斯塔馬塔科斯在一份關於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候選資格的推薦報告中,[81]卻稱讚他是「卓越的語言學家、在語言科學方面的天才」。他還指出,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在國外受過良好的教育,是許多高質量著作的作者。不過,斯塔馬塔科斯的主要論點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實際上是辜負了自己」,因為他沒有選擇客觀、科學研究的大道,而是懷着狂熱,「一路走向懸崖」。他把這看作一種「青年時期的誤入歧途」,並責備他居然還希望憑藉這些觀點(在斯塔馬塔科斯看來相當於「自毀」)來獲得獎賞,也就是通過教席的認可。斯塔馬塔科斯稱通俗語是「在某些精神領域和創造活動中值得一用的語言」,並補充說自己能夠容忍它,甚至在翻譯古代文獻時也不諱言採用其中的成分。他強調,整個通俗語運動的理論是「值得尊重和關注的」。不幸的是,正如下文所述,在那個年代通俗語被某些政治力量(如民族解放陣線)所利用,其使用與政治(而非純粹民族性的)意識形態聯繫在了一起。因此,在他的報告中寫道:「通俗語運動成了陰謀者、革命者,在希臘人的意識里被視為非法」。報告還認為,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理應像珍視眼睛一樣維護傳統,把純正希臘語視為「慈愛的母親或年長的姐姐」,而通俗語應當是「被寵愛的孩子」。相反,他卻顯得像是「弒母者、弒子者」之類。最後,按照斯塔馬塔科斯的說法,普通的文盲百姓把孩子送去學校,是為了讓他們比自己更好,主要是通過語言教育;而通俗語運動則使他們從學校里出來反而比之前更糟,其目的似乎就是要「推翻」傳統語言以及與過去相關的一切。他還在自己的《歷史語法》中發起攻擊,[82]抨擊那群「被輕率地稱為文盲」的大眾,指責他們企圖摧毀古希臘語和純正希臘語的語法。他進一步寫道,這種厭惡感出自無知,因為「人對某事理解得越深,就越會去熱愛它;反之,不理解的東西便會令人厭棄」。他的批評同樣針對當時一些訓練不足的語文學者。總體來說,斯塔馬塔科斯的觀點是:國家的受過教育的人應當指引道路,讓所有社會階層的人都能深入掌握希臘語,從而繼承古典文化。這並不意味着要連根拔除通俗語,而是認為它只應在詩歌、歌曲等領域發揮作用,總體上仍應處於次要地位。
重新點燃語言問題的是報紙《衛城》,其出版人是弗拉西斯·加夫里伊利季斯。這份報紙支持當時最為激進的普西哈里提出的語言改革。支持者如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雅科沃斯·波利拉斯等人猛烈抨擊阿提卡主義,並熱情捍衛通俗語,把它視為希臘文學的真正工具。於是,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語言問題逐漸呈現出文化層面的性質,同時也獲得了社會和政治層面的意義,甚至導致血腥衝突。1901年,亞歷山德羅斯·帕利斯在《衛城》上發表了一篇用極端通俗語翻譯的《聖經》,引發了雅典大學教授和學生的暴力抗議,最終釀成流血事件(即所謂的「福音書事件」)。不過,正如喬治斯·哈齊達基斯精準指出的那樣,福音書事件並非教授們挑起,而是學生們引發的(他甚至說,這場騷亂「無非是神的靈感……落到了學生們的腦袋裡」)。他的論據是,如果真是教授們策劃的陰謀,那麼幾年前當荷馬《伊利亞特》的通俗語譯本和其他譯本出版時,也應該發生類似事件,但當時並沒有。[83]另一個可資說明的事實是,當時格利諾斯和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竟然站在喬治斯·米斯特里奧蒂斯的支持者一邊。[84]1903年,國立希臘劇院上演了埃斯庫羅斯的《俄瑞斯忒亞》通俗語譯本,再次引發了通俗語派與純正希臘語派之間的血腥衝突(即所謂的「俄瑞斯忒亞事件」)。通俗語派的對手譏諷他們為「長發黨」,指控他們是叛徒,並聲稱他們奉行的是斯拉夫人的陰謀,目的在於分裂希臘民族、挑起宗教紛爭,以便保加利亞的牧首區能爭取到馬其頓的希臘人。語言與政治的狂熱模糊了事實:其實所有人的目標都是解放馬其頓,因為通俗語運動始終將民族與語言緊密聯繫在一起。同一時期,一個重要事件是季米特里奧斯·坦戈普洛斯創辦了文藝政治報紙《努馬斯》。它成為普西哈里斯及通俗語派的非正式宣傳陣地,儘管後來坦戈普洛斯和普西哈里斯因政治原因發生了衝突。
這一努力的重要里程碑,是1910年希臘語教育研討會的成立。參與者包括季米特里斯·格利諾斯、亞歷山德羅斯·德爾穆佐斯、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等人。該學會作為自由派通俗語運動的機構,與普西哈里斯的語言觀點保持明確的距離,[85]它採用了一種更接近純正希臘語、並受到其深刻影響的通俗語形式。與此同時,隨着沃洛斯實驗女子中學的創辦,人們嘗試進一步推廣通俗語,並加強自然科學、技術、實用課程等教育,但這也引發了反對。女子中學的創辦人兼校長德爾穆佐斯被指控敗壞風俗、傳播共產主義和無神論,然而最終被判無罪。整個民族因此分裂為兩派,語言問題的重要性急劇上升,甚至凌駕於民族自由的理念之上。這一時期不斷出現的教育改革,有的沒有通過,有的停留在紙面,其目的都是為了使教育體系適應國家的社會經濟需求。結果是,在整個50年的時間裡——從20世紀初開始——希臘的官方國語先後更替了大約九次,在純正希臘語與通俗語之間來回搖擺。
1911年,經過四天的議會辯論後,埃萊夫塞里奧斯·韋尼澤洛斯領導的政府支持使用「簡化的純正希臘語」,理由是書面語必須與口語保持一致。[86]憲法為語言的使用設定了基本框架,規定其應當與憲法本身的語言相同:「國家的官方語言,是憲法起草所用的語言,也是希臘立法文本所用的語言;任何對其的篡改都被禁止。」[87]然而,再一次,使用通俗語的人被一些人視為是在貶低傳統與宗教的價值,甚至是在攻擊既定的社會秩序。

語言成了施加暴力與權力的工具。1913年齊里莫科斯法案未能通過後,第一次在教育中確立通俗語的正式成功嘗試出現在1917年。當時,韋尼澤洛斯的臨時政府推行教育改革,規定在小學低年級使用通俗語作為教學語言。然而,隨着1920年自由黨下台,這一法律被廢止,新政府下令將用通俗語編寫的小學讀本《高山》「焚毀,因其乃虛妄之作」。改革的發起者也被革職,最終流放。在德占時期,認為使用通俗語威脅國家主權的觀念達到了頂點:約安尼斯·卡克里季斯·教授因為以通俗語和單調正寫法系統發表大學講稿,而遭到紀律審判。[88]
一個荒謬到近乎可笑的大問題,是純正語與通俗語的政治化(即使在它們最簡單的形式上)。結果就是:1917年學校里教通俗語,1921年改成純正語,1923年又改回通俗語,1926年再度換成純正語,1927年因聯合政府的緣故,兩種語言並行,1931年又用通俗語,1933年切回純正語,1939年則兩種語言並行(德占結束後則主要使用純正希臘語)。[89]這裡唯一值得注意的是:揚尼斯·梅塔克薩斯偏向通俗語,而不是純正語。
這種局面基本上一直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也許最重要的發展,是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編寫並於1941年出版了基於通俗語的《現代希臘語語法》(Νεοελληνικής Γραμματικής)。1964年,喬治·帕潘德里歐政府在教育部秘書長埃萬耶洛斯·帕帕努措斯的推動下,賦予教師自由,可以選擇使用兩種語言中的任何一種進行教學,同時兩種語言都在課堂上教授。
在軍政府獨裁時期,純正希臘語的使用被用來製造社會區隔,從而傳遞出一種信息:在政治上他們更高人一等。尤其是政治人物那種常帶含糊曖昧的語言風格,反而成為他們正當占據發言權、掌控話語權的工具。在另一邊,通俗語派則面臨嚴厲打壓。正如赫里斯蒂迪斯在《民法典》翻譯中所寫、而安娜·弗蘭古達基強調的那樣,[90]有人甚至只因寫作της αποβλάκωσης(而不是更「正統」的της αποβλακώσεως),就被扣上「國族忠誠可疑」、共產黨代理人之類的帽子,甚至徹底喪失在官方學術界發展的前景。
所謂的「現代希臘語」,最終由卡拉曼利斯政府確立為官方語言,但它與普西哈里斯的極端通俗語大不相同:它沒有方言色彩和過度激進的成分,而是吸收並融合了部分純正希臘語的元素。與此同時,共產黨的合法化也使語言問題失去了政治上的敏感性,人們不再將使用通俗語與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和混亂聯繫在一起。至於純正希臘語,它已不再是一種有效的語言工具,也不再對任何權力結構有用。1967年軍政府對純正希臘語所謂「神奇力量」的濫用,成了它的最後絕唱。[91]
語言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終於告一段落,這場紛爭持續了將近一個半世紀。1975年,康斯坦丁諾斯·卡拉曼利斯政府在新的憲法中刪去了1952年憲法裡關於語言的特別條款。[92]1976年,教育部長喬治·拉利斯提出建議,卡拉曼利斯政府隨即決定,在各級教育、國家一切運作和公文中全面使用通俗語。[93]至此,隨着通俗語在教育和行政中的正式確立,語言問題在形式上徹底解決。延續了近二十個世紀、困擾希臘教育和社會達143年的雙重語言現象終於宣告結束。
Remove ads
今天,說「在現代標準希臘語(Πρότυπη Νέα Ελληνική,簡稱PNE)中占主導的是通俗語」並不準確。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有兩點:首先,PNE在很大程度上,尤其在詞彙方面,深受純正希臘語的影響。[95]17世紀時引入的一些當時陌生的詞彙,如今已經聽起來十分自然,例如「βρέφος」(嬰兒)、「ευλάβεια」(虔敬)、「συμβουλεύω」(建議)、「οδύνη」(痛苦)等等。近年來,還有學者(如巴比尼奧蒂斯)嘗試進一步用更加書面化、古老的詞彙來充實現有的通用詞彙,比如「μεμψιμοιρία」(牢騷、抱怨)等。[96]根據1976年第309號法律,國家開始使用「沒有方言色彩和極端成分的通俗語」。也就是說,這種語言以通俗語為基礎,但去掉了它的主要特徵——方言;吸收了純正希臘語的元素,卻捨棄了其語法;結果是為通俗語提供了極為豐富的詞彙。最後,還部分保留了一些已經定型的古風短語,如「εἰρήσθω ἐν παρόδῳ」(順便一提)、「τῷ ὄντι」(的確如此)等。其次,如果追溯到民間詩歌(這些詩歌基本上是未受教育的百姓在舊時代所使用的通俗語的根基),就會發現其語言缺乏清晰統一的框架。不僅因為各地區擁有自己的方言特徵(如在克里特島,常在動詞詞幹[a/ev]與詞尾之間插入[-γ/j-],如μισεύγω;[s]或[r]後的[j]消失,如άξος代替άξιος;過去時前綴ε-變為η-,如ήφερα;摩擦音前中綴-ν-消失,如άθρωπος代替άνθρωπος;用τσι/τσή作代詞屬格;以及(ε)ίντα < τί εἶναι,即τα代替τί等),還因為不同的「通俗語派」對於所謂的「標準通俗語」存在很大分歧(參見普西哈里斯的主張)。
20世紀的通俗語擁護者主要依賴波利提斯的研究成果。波利提斯在考察了大量民歌和詩歌的民間風格後,對其基本拼寫和詞彙進行了規範化。[97]當然,這也引發了大量爭議,因為顯而易見,許多民間作品中會出於詩歌自由而使用一些陌生的詞彙和句式。部分原因在於這些作品往往以手稿形式多次被轉抄,有時由學者,有時由文盲,導致文體出現顯著差異(如《阿爾穆里斯之歌》)。這意味着,其中一些歌曲實際上是由書面語寫成的詩歌、歌曲經過口頭傳播後演變而來。通俗語與後拜占庭時期(15—18世紀)聯繫最緊密的例子,是民歌《死神與牧羊人》(Ο Χάρος και ο τσοπάνης)。不過,這首歌最早是在1860年才被刊行出來的。[98]
這種更通俗的方言在同一世紀中期由於啟蒙運動而得到更廣泛的傳播,涉及歷史、地理、政治和自然科學的著作也隨之流行開來。可是,對於當時那種未經雕琢的通俗語言來說,最大的障礙是嚴重的詞彙匱乏。這個問題要麼由學者直接借用古希臘語來彌補,要麼由非專業人士通過引入歐洲語言中已使用的外來借詞來解決。很多人甚至把在民間口語中寫不成一封像樣的信,比作一隻被剪掉翅膀的雄鷹,仍然以為自己能像從前那樣飛翔。[99]這自然又引發了新的爭論。像內奧菲托斯·杜卡斯這樣的學者認為,既然詞彙已經被報刊以規範的方式使用,那麼進一步的改革也就順理成章了,例如恢復古典語法結構(把「με」與屬格搭配而非賓格)、恢復單詞化的將來時、恢復不定式等(「若是不定式與將來時再度被引入,而一些語氣詞也發生變化,那麼不同之處又能體現在哪裡呢?」)。[100]同時,反對的聲音也存在。喬治斯·哈齊達基斯就提出反對建立以各地通俗語為基礎的公共「通俗語」,理由是方言差異和土語現象過多。他認為,既然文言元素已經被民眾完全吸收,那麼當時所謂「通俗語」所代表的民間力量其實走錯了路,於是語言之爭又一次重新燃起。[101]不幸的是,在這整個過渡時期,政治開始介入,人們僅僅因為觀點不同,就給對方貼上「法西斯」或「叛徒」的標籤。正如前面提到的,由於出現了用通俗語的翻譯(參見亞歷山德羅斯·帕利斯在《衛城》報上的譯文),雙方陣營逐漸形成,其中學生站在純正希臘語一邊,並最終占了上風。隨後,這種氛圍甚至伴隨着暴力事件(參見「福音書事件」)。「長發派」(即通俗語派)被指控為共產黨人,以及當時所謂的「斯拉夫陰謀」的同情者。就這樣,這類指控突然間逐漸坐實,通俗語派也被越來越多地同激進的共產主義左翼聯繫在一起。在這種緊張的氛圍下,越來越多的通俗語派人士開始與普西哈里斯倡導的語言拉開距離,理由不僅出於語言學的考慮,也出於政治上的顧慮。毫無疑問,這標誌着那一階段努力的結束。
幾年後,儘管特里安塔菲利季斯和德爾穆佐斯努力表明通俗語既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都與共產主義無關,但他們的努力終究落空,因為格利諾斯在1927年通過希臘共產黨轉向了馬克思主義,而該黨也從那時起開始使用通俗語——這是它自1918年以來一直迴避的做法。直到1963年,自由派的喬治·帕潘德里歐才公開宣稱在這一棘手問題上實行「平等權利政策」,不過當時希臘國家的正式書面語仍然是純正希臘語。此項新政策的結果,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的語法書首次被引入學校。然而,這本語法書很快就遭到批評,因為它幾乎沒有涉及當時已經被通俗語吸收的那些純正語成分。這場語言戰爭似乎在1974年部分塵埃落定:卡拉曼利斯自上台第一刻起就開始將通俗語作為國家的正式語言,並使共產黨合法化。至於純正希臘語,它已永遠在通俗語上留下烙印——這一點從科斯塔斯·塔赫齊斯的小說《第三個花環》中就能看出來:書中兩個平民女性的對話充滿了大量純正語成分。[102]
今天,依照喬治斯·巴比尼奧蒂斯的看法,語言問題可以被雙重理解:既有益處,也有害處。它之所以有益(是一種「福祉」),在於許多優秀的人才投入其中,從形態句法和歷史的角度對語言進行了深入分析,而這種研究在幾個世紀裡都無人涉足。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場巨大的精神資源浪費。因為在那個時代,本應投身於真正科學研究的人們,反而把主要精力耗費在無謂的批評(如科德里卡斯)、空洞的著作(如羅伊德斯的《偶像的覆滅》),或者最終演變為關於語言使用的意識形態論文上。在這一爭論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喬治斯·哈齊達基斯、約安尼斯·普西哈里斯和馬諾利斯·特里安塔菲利季斯。[103]
然而,這種突如其來的變化又產生了一個新問題(而非「爭論」),即所謂的「語言問題」。由於缺乏教材和正確指導,通俗語的質量出現了急劇下降,現代通用通俗語與早期通俗語之間出現了巨大鴻溝。[104]單調正寫法的推行改革也帶來了很大問題——甚至伴隨一些錯誤的論據,例如喬治斯·哈齊達基斯所提及的那些。[105]根據巴比尼奧蒂斯的觀點,這導致了閱讀上的困難,需要加以改進。[106]這場語言爭論(官方上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並非簡單地在兩個陣營之間展開,而是形成了多個陣營,其中較為突出的有:古希臘化派,即純正希臘語陣營(如塞奧托基斯、科萊斯等);君士坦丁堡學者的雅言方言(如卡塔爾齊斯);較為通俗的民間通用語運動(亦稱「通俗派」,如普西哈里斯、索洛莫斯);以及在拜占庭時期,極具影響力的聖經通用語陣營。
Remove ads
參見
- 語言政策
- 季米特里奧斯·韋爾納扎基斯
- 埃曼努埃爾·羅伊德斯
- 喬治斯·米斯特里奧蒂斯
- 喬治斯·哈齊達基斯
- 阿扎曼蒂奧斯·科萊斯
- 約安尼斯·維拉拉斯
- 約安尼斯·普西哈里斯
- 俄瑞斯忒亞騷亂
- 福音書事件
- 希臘語教育研討會
- 季米特里斯·格利諾斯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
